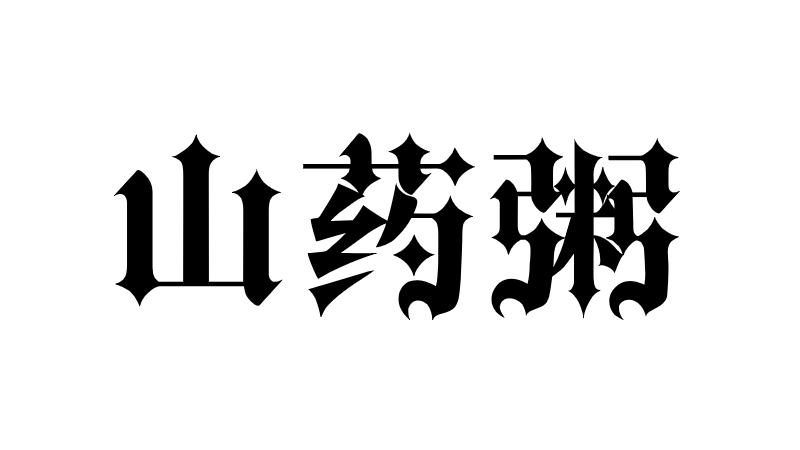
山药粥
山药粥
有时候,人们会为了不知能否实现的愿望,献出自己的一生。有人会嘲笑这种痴傻,可嘲笑者自己也不过是待在人生路边的旁观者罢了。
可是,一个卑微的、被世间迫害的小人物被人轻易满足自己多年以来的愿望,随之而来的恐怕只有幻灭感…
约摸是元庆末年、仁和[1]初年时的事了,反正不管在哪个年代,对本篇故事并没有多少妨碍。读者只要知道遥远往昔的那个平安朝是故事的背景便足够——当时,在侍奉摄政大臣藤原基经的侍从中,有某位五品[2]。
在下并不想称他为“某位”,也想弄清楚他姓甚名谁、来自何方,不巧古书上全无记载,大概他只是个不值一记的平庸之辈吧。看来古书的著者对庸人凡事无甚兴趣,这一点上,他们与日本的自然派作家[3]大相径庭。原来王朝时代的小说家并非有闲之人,这倒是出人意料。总之,在摄政大臣藤原基经的侍从中有某位五品,乃是本篇的主人公。
五品其貌不扬。他身材矮小,鼻子红通通的,眼角耷拉着,髭须自然是稀稀拉拉,脸颊削瘦,下巴颏又异常窄小,嘴唇嘛……若是一一道来,简直没完没了。总之,我们这位五品的相貌便是这么一无是处,全不成个模样。
五品是何时、因何种缘故来侍奉基经大臣的,无人知晓。不过确凿无疑的是,从老早以前,他就穿一件褪了色的袍子、戴一顶瘪瘪的乌帽,不厌其烦地每天做着同样的差事。结果,现在任是让谁来说,都想象不出五品曾经年轻过(五品已四十开外)。仿佛他一生下来,就有这般寒颤颤的红鼻头、稀拉拉的胡须,吹着朱雀大街上的凉风。在无意识中,上至主公基经,下至放牛的童儿,在无意识中都对此深信不疑。
五品既是这般模样,周围人对他的态度自然毋庸多说了。侍从官舍中的同僚们对五品全不在意,仿佛他还不如一只苍蝇。位阶低于五品的侍从,不管有无官品,共有将近二十人,眼见五品出出进进,他们只管漠然以对,态度之冷淡令人诧异。便是五品有所吩咐时,他们也照样闲聊天,决不会停嘴。对他们来说,就像看不见空气一样,五品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存在。下级侍从尚且如此,别当、舍监等长官们对五品不瞅不睬,更是理所当然了。对于五品,他们在冷淡的表情底下,隐藏着孩子般无意识的恶意,不管吩咐什么,都用手势一挥了事。但人类之所以需要语言,并非出于偶然,单靠手势无法表达的情形,自然时而有之。此种情况下,他们便归结为皆因五品的悟性不足所致。因此,当五品不能领会时,他们便盯着五品,从他歪扭扭的软乌帽,到破旧的稻草鞋,上看下看,打量千遍万遍,末了鼻子里嗤笑一声,拂袖而去。即便如此,五品也并不气恼。他就是这么怯懦软弱,甚至感觉不到这所有的不公平。
可是,同僚侍从们得寸进尺地戏弄他。年纪大的同僚拿他不体面的相貌当噱头,讲些陈词滥调的俏皮话,年轻的同僚也趁机轻嘴薄舌、插科打诨。他们在五品面前评论他的鼻头胡须、乌帽官袍,说个没完。这还不算,就连五六年前已经和五品分开的“地包天”媳妇,以及传说和媳妇有染的酒鬼和尚,都屡屡成为话题。更有甚者,他们还干出不少恶劣的恶作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比如他们喝掉五品竹筒里的酒,在里面换上尿,仅举此一例,余下的可想而知。
不过,对这些揶揄嘲弄,五品却全无感觉,至少在旁人看来,他像是全无感觉。无论人家说什么,五品都神色不变,默默抚摸着稀拉拉的胡须,若无其事地该干吗干吗。唯有在同僚的恶作剧太过分时,比如把纸片粘到他发髻上、草鞋系在他刀鞘上之类,他会堆起笑脸——其实到底是哭是笑,也看不分明——说,“休要如此啊,诸位兄台”。看到他的模样、听到他的声音的人,一时间都会被一种怜悯感打动(被他们欺负的绝不止红鼻五品一人,他们所不知道的某人——为数众多的某人,借着五品的模样与声音,来谴责他们的无情)。此种感觉尽管朦朦胧胧,但一瞬间确实渗入了他们的心里。不过,能够把这一瞬间的心情长久保持下去的人,就极其稀少了。
在这极少数人中,有一个尚无官品的侍从。他来自丹波国[4],是个鼻子下刚刚长出柔软茸毛的青年。当然,青年一开始也像众人一样,毫无理由地看不起红鼻五品。可是有一天他碰巧听见了“休要如此啊,诸位兄台”,这声音在他头脑里萦绕不去。那之后,在青年眼里五品和从前判若两人。从五品那营养不足、面色苍黄、木讷迟钝的脸上,能够看到一个为世间迫害而哭泣的“人”。每当这位尚无官品的侍从思考五品的问题时,他便感觉世间万物骤然暴露出低劣下作的本质。与此同时,那霜打般的红鼻子、稀疏可数的胡须,却给他心里带来一丝安慰……
但这想法仅限于他一人。除此之外,五品依然在周围人的轻蔑中,继续过着狗一般的生活。先说,他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他有一件灰蓝袍子,一条同色的宽腿袴,都褪了色,变得蓝不蓝、青不青。袍子倒还罢了,只不过肩膀处塌了些,圆纽的带子和菊花襻变了色,宽腿袴的下裾却已经破碎得不成样子。宽腿袴底下没有穿衬裤,时而露出瘦腿来,看到这番光景,即便嘴巴不刻薄的同僚,也觉得他再寒碜不过,活像拉着落魄公卿破车的瘦牛一般。此外,他的佩刀也不成个体统,刀柄上的贴金褪了色,刀鞘上的黑漆也斑驳剥落。五品便顶着那个红鼻头,踢踢踏踏地拖着草鞋,原本腰板就不直,大冷天里更是拱肩缩背,他迈着小碎步,眼馋似的东张张西望望。就凭这副尊容,难怪连过路的商贩都瞧不起他。实际上,还真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那天,五品要去神泉苑,路过三条坊门时,看到五六个孩童围在路边。五品心想或许他们在打陀螺,就从后面瞥了一眼,谁知他们在一只迷路的狮子狗颈上拴了绳子,正抽打着玩呢。五品生性胆小,以前纵然同情什么,顾忌着别人,从来没敢付诸行动。但这一次他看对方是些孩童,遂鼓起了几分勇气,努力做出笑脸,拍拍领头孩子的肩膀,说道:“喏,你们就饶过它吧。就算是只狗,挨打也会疼的哪。”那孩子回过头来,翻着白眼,轻蔑地打量五品,那神气和上司在五品不能领会他意图时的表情,恰恰如出一辙。“要你多管闲事!”孩子退后一步,傲慢地撇着嘴,“你这个红鼻头!”听了这话,五品仿佛被打了一记耳光,但他决不是因为听了恶言恶语感到恼火,而是因为自己多嘴多舌,丢人现眼,觉得羞愧难当。他苦笑着掩饰住自己的尴尬,默默地朝神泉苑方向走去。身后,六七个孩童凑到一起,对着他做鬼脸、吐舌头。当然,五品并没看见,可是就算他知道了,这么没脾气的五品,又能怎么样呢?
不过,若说本篇故事的主人公生下来就是为了被人看不起,心里没有一丁点儿希望,那倒也不尽然。自打五六年前,五品就对一种叫作山药粥的东西异常喜爱。山药粥就是将山药切碎,用甜葛汁煮成的粥,当时被视为无上的美味,甚至被端上万乘之君的御案。因此,像我们五品这等人物,只有在一年一度、摄政大臣家举行大宴之际,方能尝尝山药粥的味道。但即便那种时候,喝到的山药粥也仅够润润喉咙。所以,能将山药粥喝个够,从很久以前便成为五品唯一的愿望。自然,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话。不,或许就连五品自己,也没有清晰意识到这是贯穿了他一生的愿望。但其实,甚至不妨说五品就是为了这个活着的。——有时候,人们会为了不知能否实现的愿望,献出自己的一生。有人会嘲笑这种痴傻,可嘲笑者自己也不过是待在人生路边的旁观者罢了。
可没想到,五品的“将山药粥喝个够”的梦想,却出乎意料地轻易实现了。本篇山药粥故事的目的,就是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且说这年的正月初二,藤原基经的府中举行摄关家大宴(摄关家大宴是由摄政关白家招请大臣以下的高官的宴会,与两宫的大飨宴同日举行,与大飨宴差别不大[5])。五品也同其他侍从一起享用大宴的残肴剩馔。当时尚没有将酒宴残肴舍给下等人的风习,而是由府中侍从聚集一堂分而食之。说是与大飨宴无甚差别,终究是古时候的酒宴,肴馔种类虽多,却并无什么珍馐,无非是些蒸年糕、炸糕、蒸鲍鱼、干鸡肉、宇治小香鱼、近江鲫鱼、干鲷鱼条、盐渍带籽鲑鱼、烤章鱼、大虾、大柑子、小柑子、蜜橘、柿饼串儿之类。不过,其中就有山药粥。五品年年盼着山药粥,可惜总是人多粥少,能进自己嘴里的没几口。而且今年的山药粥尤其少,或许是心理作用,便觉得比以往更美味。五品恋恋地端详着喝光了的空碗,手掌擦掉稀拉拉胡子上沾着的粥滴,自言自语道:“什么时候才能喝个够哪?
“大夫阁下还没尽兴喝过山药粥?”
五品的话音未落,便有人嘲笑道。那声音粗豪雄壮,五品挺直驼肩,怯怯地朝那人看去。声音的主人乃是民部卿藤原时长之子藤原利仁,当时同五品一样,担任基经的侍从。利仁是个身长肩宽、高大魁梧的伟男子,他一边嚼着煮栗子,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黑酒,已经醉醺醺的了。
“好可怜哪。”
见五品抬起头来,利仁继续说道,语气半是轻蔑,半是怜悯。
“阁下要是愿意,在下就让你喝个够。”
一直被欺负的狗,就算偶尔给它块肉,它也不会轻易凑过来。五品又露出了那分不清是哭还是笑的笑脸,一会儿看看空碗,一会儿再看看利仁的脸。
“不愿意?”
“……”
“怎样?”
“……”
五品觉察到,这一会儿工夫,众人的视线都盯在了自己身上。只要他一搭腔,肯定要受到大伙儿的嘲弄。他甚至觉得,不管自己回答什么,都会被看不起。五品踌躇不决,若不是对方有些不耐烦地说“若不愿意,在下决不强求”,他八成会一直对着空碗和利仁的脸看个不休。
于是,五品慌忙答道:
“哪里……不胜感激。”
听到这句回答,众人顿时哄堂大笑。甚至有人模仿五品的腔调,说着“哪里……不胜感激”。在盛着黄橙红橘的高盘矮盏间,一大堆软乌帽、硬乌帽和着笑声,像波涛一样此起彼伏。其中,笑得最响亮、最畅快的,便是利仁自己。
“那么,在下不久便来相邀。”说着,利仁微微皱了皱眉,涌上来的笑和刚咽下去的酒在喉咙处挤成了一团,“如此可好?”
“不胜感激。”
五品红着脸,吭吭哧哧重复了一句。不必说,众人又大笑了一番。利仁故意叮问,就是为了逗五品说这句话,这回他仿佛觉得比刚才更滑稽,抖动着肩膀哈哈大笑。这个朔北的粗豪汉子,只晓得两种生活之道,一是饮酒,二是大笑。
不过,幸好谈话的中心很快从二人身上移开了。因为尽管是嘲弄取笑,若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红鼻五品身上,也难免会有人感到不快。总之,话题一个接一个,酒菜也渐渐变少,后来有人说起某个寮生侍从[6]骑马的时候,把两条腿都塞进了护腿袴单侧的裤筒里,才重新聚起了满座的兴致。唯有五品对这些话题似乎全然听而不闻,也许“山药粥”三个字已经占据了他所有的思维吧。烤雉鸡肉放在面前,他不动筷子,黑酒就在手边,他也不沾唇。他只管双手放在膝上,像相亲时的大姑娘似的羞羞答答,脸一直红到了点点染霜的鬓边,一个劲儿盯着空空如也的黑漆碗,傻呵呵地微笑着。
四五天后的一个上午,两名骑马的男人沿着加茂川河畔,在通往粟田口的大路上缓辔而行。一人身穿缥青色狩衣和同色宽袴,佩一把镶金嵌银的大刀,是个“须黑鬓美”的男人。另一人穿着破旧的深蓝袍,只套了一件薄薄的棉袄,是个约摸四十上下的侍从,不管是那系得歪歪扭扭的衣带,还是沾着鼻涕的红鼻头,通身上下没一处不显得寒碜可怜。不过两匹马倒都是良驹,前面桃花马,后面菊花青,只有三岁牙口,神骏非凡,惹得过路的商贩和差人纷纷注目。此外,还有两人紧紧地跟随在马后,那是背弓和牵马的随从。——不必多说,这正是利仁和五品一行人。
虽然正值寒冬,却是个安宁晴和的好天气,一点微风也无,水流潺湲,河滩白色的石子间,艾蒿枯萎的叶子纹丝不动。临河的矮柳树叶子落尽,光溜溜的树枝迎着光滑如饴的阳光,树梢上的鹡鸰鸟尾巴稍稍一动,便在大路上投下清晰的影子。暗绿色的东山上方,露出了一坨圆圆的山肩,仿佛霜打过的天鹅绒,那大概便是比睿山[7]吧。马鞍上的螺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两人并不加鞭,向着粟田口悠悠地信马而行。
“您说要带在下出门,要去哪里?”五品手法生涩地拉着缰绳,问道。
“马上就到了,不必担心,不远。”
“是粟田口附近?”
“暂且这么想也无妨。”
今早,利仁邀请五品说东山附近有温泉,不妨去玩玩。五品信以为真。他很久没泡澡了,这一阵子只觉浑身发痒。若能吃过山药粥,再泡泡温泉,真是不敢奢望的福分呢。如此一想,五品便跨上了利仁吩咐人牵来的菊花青。可是,两人并辔来到此地,却发现利仁的目的地似乎并不在这儿附近。实际上,不知不觉中,粟田口已经过了。
“不是去粟田口吧?”
“再稍微往前走一点。”
利仁含着微笑,故意不看五品的脸,静静地驱马前行。路两边的人家逐渐稀少,寥廓的冬季田野上,随处可见觅食的乌鸦,山阴处尚未消融的残雪泛着微微的青色。黄栌树尖锐的枝梢直刺入天空,虽是天色晴朗,但也令人感到些许寒意。
“那么,是去山科附近?”
“山科就在这里嘛。再向前些。”
的确,说话间已经过了山科。何止如此,不觉中又把关山甩到了身后。稍稍过午时分,终于到了三井寺前。三井寺中有位与利仁私交甚密的僧人,两人拜访了僧人,叨扰了一顿午饭,随后又上马急急赶路。较之方才来时路上,接下来的路段人烟大为稀少,尤其是当时盗贼横行四方,世道并不太平。五品把驼背弯得更低了,仰望着利仁的脸,问道:
“还要往前走?”
利仁微微发笑,仿佛是恶作剧快要得逞的孩童面对长辈时的微笑。鼻头处堆起的皱纹,眼角上漾着的褶儿,都像是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大笑。终于,他说:
“其实,我是要带阁下去敦贺。”
利仁大笑着,举鞭指了指远处的天空。马鞭下方,近江湖水映着午后的阳光,灿灿地闪烁着白光。
五品大为惊慌。
“您说的敦贺,是越前的敦贺吗?是那个越前的……”
利仁乃是敦贺的藤原有仁的女婿,经常住在敦贺。五品平日里并非没有听说过这事,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利仁竟要把自己带到敦贺去。先说,要去隔着恁多山山水水的越前国,像这样仅带着两名随从,怎可能平安到达?何况这一阵子,四处都有传言说旅人被盗贼杀害。五品哀求地看着利仁,说:
“这怎么使得!在下本以为去东山,结果到了山科。以为是山科,结果又去三井寺。最后竟是越前的敦贺,到底怎么回事?若您一开始就说去敦贺,也可多带几名下人。——去敦贺,可怎么使得!”
五品嘟嘟囔囔,几乎要哭出来。若不是有“将山药粥喝个够”来鼓舞他的勇气,他恐怕会就此作别,独自回京都去。
“有我利仁一人在,足可当得千人。旅途中的事,你不必担忧。”
看到五品的狼狈模样,利仁微蹙起眉毛嘲笑道。随后,他唤来背弓的随从,取过箭壶背在背上,又拿过黑漆雕弓横在鞍上,一马当先往前走去。如此一来,怯懦的五品别无他法,只能服从利仁的意志。五品战战兢兢地张望着四周荒凉的原野,嘴里念叨着模糊记得的观音经,红鼻头几乎蹭到了马的前鞍桥上,跌跌撞撞地前行。
马蹄声回荡在原野上,野地里覆盖着苍茫的黄茅草,随处可见的水洼里清冷地倒映着蓝天,使人疑心这冬日的午后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冰冻住。原野尽头是一带山脉,或许是背阴的缘故,山体被抹上了连绵悠远的暗紫色,丝毫不见残雪闪耀的荧光。不过,这景色被数丛萧瑟的枯芒草所遮蔽,无法映入两名随从的眼中。——忽然,利仁转向五品,说:
“看,那边来了个好使者,命它去敦贺传话吧!”
五品没听明白,怯怯地顺着弓所指的方向望去。那里本就不见人迹,只有野葡萄之类的藤蔓缠绕着一丛灌木,其间有一只狐狸,一身暖融融的毛色,沐浴着西斜的日光,正慢悠悠地走着。突然,狐狸惊慌腾身,拼命奔逃起来,原来是利仁猛然挥起响鞭,纵马冲了过去。五品也忘乎所以,跟在利仁身后追去,随从们当然不肯落后。一时间,马蹄嗒嗒地踢着石子,打破了旷野的宁静,片刻之后,利仁止住了马,却见狐狸已不知何时被抓住,被提着后腿倒悬在马鞍旁。想必是利仁将狐狸逼得无路可逃,将它制伏在马下,从而擒获的吧。五品慌忙擦着稀疏胡子上的汗珠,赶到利仁身旁。
“呔,狐狸,你听好了!”利仁把狐狸高高地举到眼前,一脸威严,吩咐道,“今天夜里,你到敦贺的利仁府上,传我的话,就说‘利仁正与客人一道归来。明日巳时,派遣家人到高岛迎接,并带上两匹备好鞍的马’。明白了?休要忘记!”
话音刚落,利仁猛地一挥手,把狐狸抛向远处的草丛。
“嗬,跑了,跑了!”
两名随从总算撵了上来,望着狐狸逃走的方向,拍手叫嚷着。那小兽背上披着落叶般的色泽,顾不得避开树根石子,在夕阳中一溜烟地奔逃。从一行人所在之处看去,这光景历历在目。在追逐狐狸时,他们不觉来到了旷野的高处,野地伸展开舒缓的斜面,正与干涸的河床连为一体。
“真是个靠不住的使者啊。”
五品流露出纯真的尊敬与赞叹,对利仁这位粗生野长、连狐狸都能颐指气使的豪杰,五品再度肃然起敬。他已经无暇思考自己和利仁之间是何等天悬地隔,只一味地感到安心。利仁的意志所掌控的范围越广,包含在这一意志中的自己的意志,仿佛也就能够得到越多的自由。——阿谀这一行为恐怕就是在此种情况下,极为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列位看官,即便从今后五品的态度中发现某些奉承讨好的成分,也不可凭此就对他的人格妄加怀疑。
狐狸被抛出去后,连滚带爬地奔下斜坡,敏捷地跳过干涸河床的石子间,迅速冲向对面的斜坡。它一边朝上跑,一边回头望去,抓捕过自己的武者一行,还在远远的斜坡上并马伫立,看上去都只有巴掌大小。桃花马和菊花青沐浴着落日的余晖,浮现在包含着霜意的空气中,比描画出的还要清晰鲜明。
狐狸转过头去,在枯萎的芒草间风一般地疾驰而去。
翌日,一行人如期于巳时到达高岛附近。这是个毗邻琵琶湖的小村落,与昨日不同,天空阴沉沉的,几间草屋稀疏地点缀其间,透过岸边松树的枝叶间隙,可以看到湖面荡漾着灰色的涟漪,像一面疏于拂拭的镜子,泛出清冷的气息。利仁回头看看五品,说:
“看那边,下人们来迎接了。”
的确,有二三十名家仆正从岸边的松树间匆匆赶来,他们有的骑马,有的徒步,牵着两匹备好鞍的马,衣袖在寒风中翻动。片刻之间,他们已到了近前,骑马的人慌忙滚鞍下马,徒步的人屈膝蹲踞道旁,都恭恭敬敬地静待利仁。
“看来,狐狸确实去报信了。”
“那畜生生来通灵,办这点事根本不算什么。”
五品和利仁说着话,走到家仆们跟前。“辛苦了。”利仁慰劳了一句,蹲踞着的家仆们慌忙站起来,为两人牵马,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昨夜发生了一件稀奇事。”
两人下了马,正要坐到皮褥子上时,一个身穿桧皮色袍子、白发苍苍的仆人走到利仁面前,禀告道。
“何事?”
利仁一边示意五品享用家仆们带来的竹筒酒和点心,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一事禀告大人,约摸在昨晚戌时,夫人忽然不省人事,口中说道:‘我乃坂本之狐,今日受大人吩咐前来传话,你等上前来,仔细听着。’于是众人上前聆听,夫人的话大意为,‘大人如今正偕同客人归来,你等派人明日巳时到高岛迎接,且带上两匹备好鞍的马。’”
“这真是稀有之事哪。”五品看看利仁,又看看家人,讨好似的附和道。
“还有,夫人不仅说了这番话,还瑟瑟发抖,仿佛十分惶恐,说:‘莫要去迟了。若是去迟了,我会被大人休弃。’说着哭泣起来。”
“然后呢?”
“然后夫人就昏昏睡去,直到小人们出门时,夫人还未醒来。”
“怎样?”听仆人说完,利仁得意地看着五品,“咱家连畜生都使唤得动。”
“真真匪夷所思。”五品搔着红鼻头,微微低下头,随后,他故意惊愕地张开嘴巴,胡须上还沾着刚才喝过的酒滴。
那天晚上,利仁府中的一间屋子中,五品在长夜里辗转难眠,不经意地眺望着矮灯台的火苗。想起傍晚抵达此处之前,自己和利仁、随从们一边谈笑,一边经过松林茂密的山丘、小河、枯野,还有草丛、树叶、石子、野火的烟味儿……这些风景一一浮现在五品心头。尤其当在茶褐色的雾霭中终于抵达利仁府时,看到长火盆中那红红的火苗,心里是多么安泰——如今躺在这里,那种安泰的心情似乎也成了十分久远前的事了。盖着四五寸厚的黄棉被,五品舒舒服服地伸开腿,蒙眬地打量着自己的睡姿。
在棉被底下,五品还穿着两件利仁借给他的淡黄色厚棉衣,身上暖融融的,一动就要出汗。枕边的一窗之隔,外面就是寒霜凛冽的宽阔庭院,可自己是如此陶然自得,全无苦寒之感。比起自己在京都的寒舍,一切都如同云泥之别。但尽管如此,我们五品心里却七上八下,隐隐有种不安。他盼望时间快点过,但与此同时,他又希望天亮——也就是吃山药粥的时刻不要那么快到来。这两种矛盾的情感相互冲突,境遇的剧烈改变使心境也不得安稳,正如今日的天气似的,令人感到些许寒意。这一切都困扰着五品,结果,眼下难得的温暖也难以使他酣然入梦。
就在这时,五品听到外面宽阔的庭院中,有人在大声说话。听那声音,似乎是今天在路上迎接他们的那位白发老仆。老仆正在吩咐什么,干涩粗哑的声音在寒霜中回响,仿佛寒冷的北风,一字一句地刺进了五品的骨头中。
“下人们听好了!大人吩咐,明早卯时前,每人各带一根五尺长、三寸粗的山药来。莫要忘记,卯时前带来!”
如此这般吩咐了两三遍,不一会儿,人声消散,四周顿时像方才一样,恢复了冬夜的寂静。一片寂静中,矮灯台的灯油嗞嗞作响,红丝绵般的火苗轻轻摇动。
五品把一个呵欠憋了回去,又沉浸在漫无边际的遐想中。要下人们带山药来,不用说是为了做山药粥。如此一想,方才因为注意外面的动静而忘却了的不安,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五品心中。不想那么快吃到山药粥——这种心理比先前越发强烈,执拗地占据着五品的思绪,不肯消退。若是“将山药粥吃个够”这一愿望如此轻而易举地实现,那么他这许多年来苦苦忍耐,一直期盼到今天,又是多么无谓的辛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突然出现某种障碍,无法喝到山药粥,后来障碍又消除,费尽周折终于完成心愿,事情能这么进展就好了。这些念头像陀螺似的骨碌碌旋转着,不知不觉中,由于旅途的疲劳,五品酣然入睡。
翌日一早,五品睁开眼睛,立即记起了昨晚山药的事,急忙将房间的悬窗推起,往外张望。他不觉睡过了头,此时大约已经过了卯时。宽阔的庭院里铺了四五张长草席,上面堆着两三千根圆木似的东西,像小山一般,几乎与斜挑的柏木皮屋檐一般高。定睛一看,那全都是五尺长、三寸粗、大得不像话的山药。
五品揉着惺忪的睡眼,心头袭来一阵近乎骇然的惊愕,只怔怔地看着四周。宽阔的庭院里有数处新打上了木桩,架起了五六口能盛五石米的大锅,几十名穿着白布夹袄的年轻女仆在那里忙活。她们有的生火,有的拨灰,有的把甜葛汁从新白木桶中舀到锅里,都在准备熬山药粥,忙得团团转。锅下冒起的烟,锅里腾起的热气,与尚未全然消散的晨雾融在一起,使宽阔的庭院笼罩在一团灰蒙蒙之中,连视线也变得不甚分明,只有锅下熊熊燃烧的火焰红彤彤的。眼前所见、耳中所闻的皆是一片喧闹,仿佛到了战场或是火场一般。
时至如今,五品才寻思道,这些巨大的山药,就要在巨大的五石米大锅里变成山药粥,而自己正是为了吃这山药粥,特地长路迢迢地从京都来到越前的敦贺。五品越想越觉得,这些事没一件不令自己难堪。实际上,我们五品那值得同情的胃口,此时已经倒掉了一半。
半个时辰后,五品、利仁,以及利仁的岳父有仁,一同坐到了早膳的案前。面前的银提锅里满满地盛着约一斗山药粥,如海水一般洋洋欲溢,令人望而生畏。先前,五品看到几十个年轻人灵巧地挥着薄刀刃,把堆到房檐高的山药,从一端麻利地切碎,女仆们则跑来跑去,捧起碎山药放入大锅,拾掇得干干净净。最后,长草席上一根山药也没有了,大锅中热腾腾地冒出几股气柱,混着山药味儿、甜葛味儿,直升入早晨晴朗的天空中。五品亲眼目睹了这番情景,所以当他看到提锅中的山药粥时,嘴里还没有尝到,腹中却已感到饱胀——这怕是也在情理之中吧。五品面对提锅,难为情似的擦拭着额头的汗水。
“听闻阁下还没有尽情喝过山药粥,请多用些,莫要见外。”
岳父有仁吩咐童儿,又将几只银提锅摆到食案上,每只锅里都满满地盛着山药粥。五品闭了闭眼,原本红通通的鼻子越发红得厉害,他将大约半提锅山药粥舀进一只大陶碗里,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正如家父所言,请您务必不要客气。”
利仁坏心眼地笑着,劝他再喝一锅。五品吃不消了,若是真的不必客气,他根本连一碗山药粥也不想喝。刚才他努力忍耐,好不容易喝了半锅,要是再喝的话,恐怕没等下咽,就要吐出来。但若是不喝,便会辜负利仁和有仁的盛情厚意。于是,五品又闭着眼,喝下了剩下半锅粥的三分之一。然后,他一口也喝不动了。
“实在感激不尽,在下已经足够了。哎呀,实在感激不尽。”
五品语无伦次地说道。看上去他确实已经忍受不了,胡须上、鼻尖上汗珠滚滚,简直不像是在大冬天里。
“您用得太少,客人还是太见外了。喂,你们愣着干什么?”
听了有仁的话,童儿们又从新的提锅中为五品舀粥。五品挥舞着双手,像赶苍蝇似的,坚决辞谢。
“不要不要,已经足够了……失礼了,在下已经足矣。”
这时,利仁突然指着对面的屋檐,说了声“看那边”!若不是如此,恐怕有仁还会没完没了地劝五品喝粥。谢天谢地,利仁的叫声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到了屋檐那边。柏树皮修葺的屋檐上晨晖洒落,一只动物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屋檐上,润泽的皮毛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正是前天利仁在荒野中捉住的坂本野狐。
“狐狸也想来喝粥哩。喂,你们给它点吃的。”
利仁一声吩咐,下人们立刻照办,狐狸从房檐上跃下,也到庭院里喝山药粥了。
五品望着正在喝粥的狐狸,心里不无怀恋地想起了来到此处之前的自己。那是被许多侍从愚弄的他,那是连京城的儿童都敢骂“你这个红鼻头”的他,那是穿着褪色的外褂和宽腿袴,像流浪的狮子狗似的在朱雀大街上彷徨的、孤独可怜的他。但同时,那又是独自一人珍重地守护着“把山药粥喝个够”这一愿望的、幸福的他。——总算不必再喝山药粥了,五品放下心来,这时,他感觉到满脸的汗水渐渐从鼻尖处开始干起。尽管天气晴朗,敦贺的清晨还是寒风沁骨。五品慌忙捂住鼻子,却忍不住对着银提锅,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作者:芥川龙之介(1916年8月) 译者:赵玉皎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 元庆(877—885)和仁和(885—889)都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年号。 ↩
- 日本古代官阶的第五等,可分为正五品和从五品。下文中的“大夫”是对五品官阶的通称。 ↩
- 自然主义文学是明治中后期席卷日本文坛的文艺思潮,以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为奠基之作。自然主义文学关注凡人琐事,主张纯客观描写,后期作品的内容和格调愈见灰暗颓废,陷入自我暴露与自我告白的窠臼,故而芥川在文中加以揶揄。 ↩
- 日本旧地名,位于今京都府北部和兵库县的一部分,在平安时代近乎是“鄙俗村野”的代称。 ↩
- 此段为芥川原注。摄政和关白均为最高官职,摄政大臣通常在天皇未成年时代行政务,关白则是天皇成年后辅佐政务。平安中期为摄关政治的最盛期,此二职一般由天皇的外祖父或母舅担任,为藤原氏垄断。两宫指皇后、皇太子,每年正月初二,皇后和皇太子宫中赐宴款待前来拜贺的亲王、大臣,摄关家则宴请位阶次一等的高官。 ↩
- 在大学寮中有学籍的侍从。大学寮是日本古代律令制下培养官吏的机构,教授贵族子弟经学、律法、算学等。 ↩
- 比睿山是日本的佛教名山,位于京都市东北,自古被视为守护皇城的灵山。由于山上有天台宗的本寺延历寺,因而又被称为天台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