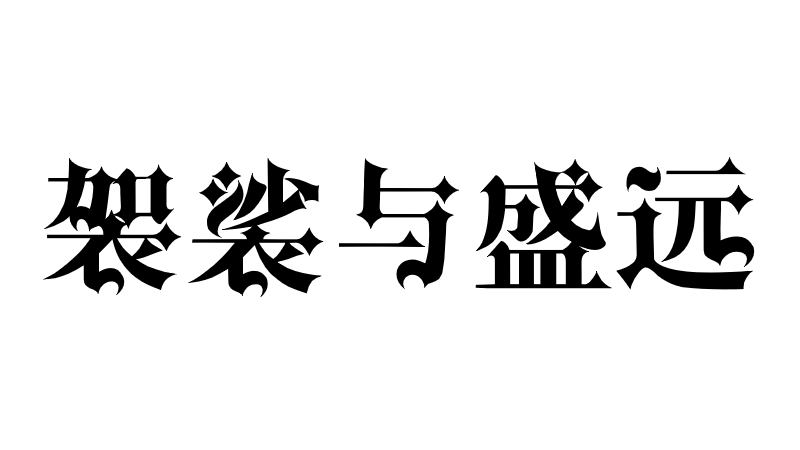
袈裟与盛远
袈裟与盛远
上
夜晚,盛远在泥墙外远眺月华,一边踏着落叶,心事重重。
独白
月亮已上来了。向来都迫不及待企盼月出,可惟独今夜,倒有点害怕月色这般清亮。迄今的故我,将于一夜之间消失,明天就完全是个杀人犯了;一想到这里,浑身都会发颤。两手沾满鲜血的样子,只要设想一下就够了。那时的我,自己都会觉得恁地可惜。倘是杀一个恨之入骨的对手,倒也用不着如此这般于心不安,但今夜所杀,是一个我并不恨的人。
他,我早就认识。名叫渡左卫门尉,倒是因为这次的事儿才知悉的。作为男人,他过于温和,那张白净脸儿,忘了是什么时候见的了。得知他就是袈裟的丈夫,一时里确曾感到嫉妒。可是,那种嫉妒之情,此刻在我心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如春梦了无痕。因此,渡尽管是我的情敌,但我对他既不憎也不恨。唉,倒不如说,我对他有点同情更好。听衣川说,渡为博得袈裟青睐,不知费了多少心思;我现在甚至觉得,这男子还挺讨人喜欢的。渡一心想娶袈裟为妻,不是还特意去学了和歌的么?想起赳赳武士居然写起情诗来,嘴角不觉浮起一丝微笑。但这微笑绝无嘲弄意味,只是觉得那个向女人献殷勤的男子煞是可爱。或许是我钟爱的女子引得那男人巴结如许,他的痴情,对身为情夫的我,带来莫大的满足也未可知。
然而,我爱袈裟能爱到那种程度么?对袈裟的爱,可分为今昔两个时期。袈裟未嫁渡之前,我就爱上她了。或者说,我自认为在爱她。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恋情,很不纯正。我求之于袈裟的是什么呢?以童男之身,显然是要袈裟这个人。夸张些说,我对袈裟的爱,不过是这种欲望的美化,一种感伤情绪而已。证据是,和袈裟断绝交往的三年里,我对她的确没有忘情。倘如在此前,同她有过体肤之亲,难道我还会不忘旧情,对她依然思念不已么?羞愧管羞愧,我还是没有勇气作肯定回答。在这之后,对袈裟的爱恋中,掺杂着相当成分的对不识的软玉温香的憧憬。而且,心怀愁闷,终于发展到了如今既令自己害怕,又教自己期待的地步。可现在呢?我再次自问:我真爱袈裟吗?
然而,在作出回答之前,尽管不情愿,也还得追叙一下事情的始末根由。——在渡边桥做佛事之际,得与阔别三年的袈裟邂逅。此后的半年里,为了和她幽会,我一切手段都用上了,而且次次奏效。不,不光是成功,那时,正如梦想的那样,与她有了体肤之亲。那时左右我的,未必会像上文说的,是出于对不识的软玉温香的渴慕。在衣川家,与袈裟同坐屋里时已发觉,这种恋慕之情,不知何时已淡薄起来。因为我已非童身,斯时斯地,欲望已不如当初。但细究起来,主要原因还是那女人姿色已衰的缘故。实际上,现在的袈裟已非三年前的她了。肤肌已然失去光泽,眼圈上添出淡淡的黑晕。脸颊和下巴原先的那种美腴,竟出奇般地消失了。惟一没变的,要算那水汪汪黑炯炯的大眼睛啦。这一变化,于我的欲望,不啻是个可怕的打击。暌隔三年,晤对之初,竟不由得非移开视线不可。那打击之强烈,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么,相对而言,已不再迷恋那女人的我,怎么又会和她有了关系呢?首先,是种奇怪的征服心理在作祟。袈裟在我面前,把她对丈夫的爱,故意夸大其辞。在我听来,无论如何,只感到是虚张声势。“这个娘儿们对自己丈夫有种虚荣”,我这么想。“或许这是不愿意我怜悯她的一种反抗心理也未可知”,我转念又这么想。与此同时,想要揭穿这谎言的心思,时时刻刻都在强烈鼓动着我。若问何以见得是谎言呢?说是出于我的自负,我压根儿没理由好辩解的。可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那纯是谎言。至今深信不疑。
不过,当时支配自己的,并非全是这种征服欲。除此之外——仅这么说说,就已觉羞愧难当了。除此之外,纯粹是受情欲的驱使。倒不是因为同她未有过体肤之亲的一种渴念,而是更加卑鄙的一种欲望,不一定非她不可,纯为欲望而欲望。恐怕连买欢嫖妓的人,都不及我当时那么卑劣。
总之,出于诸如此类的动机,我和袈裟有了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戏侮了她。而现在,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唉,关于我究竟爱不爱袈裟,哪怕对自己也罢,事到如今,已无须再问了。倒不如说,有时我甚至感到她可恨。尤其是事后,她趴在那里哭,我硬把她抱起来时,觉得袈裟比我还要无耻。垂下的乱发也罢,脸上汗涔涔的剩脂残粉也罢,无不显出这女人身心的丑恶。如果说,在那以前,我还爱她,那么,从那天起,这爱便永久的消失了。或者不妨说,截至那天,我从没爱过她,而自那以后,我心里反而生出了新的憎恨。可是,唉,今晚,不正是为一个我不爱的女人,想去杀一个我不恨的男人么?
这决不是谁之过。是我自己公然说的。“不是想杀渡吗?”——想起当时对她附耳细语时,连我都怀疑自己在发疯。可我居然这么说了。尽管竭力忍着,心想别说,终究还是小声讲了出来。回想当时为什么要讲,自己至今也弄不明白。如果这样想也未尝不可,那就是我越瞧不起她、越恨她,就越发忍不住想凌辱她。惟有杀了渡左卫门尉——袈裟所炫耀的这个丈夫,而且不管她愿不愿意,都得通她同意,才能让我称心。我仿佛被噩梦魇住一般,竟违心地一味劝她去谋杀亲夫。然而,若说我想杀渡,没有充分的动机,那就只能说是人间不可知的力(说是魔障也成),在诱使我的意志走入邪道,除此以外,别无解释。总之,我很固执,三番五次在袈裟耳边响咕此事。
过了会儿,袈裟猛地抬起头来,坦率告诉我,同意我的计划。可我对这简捷的回答,不止是意外。看袈裟的脸,有种迄今未见过的,不可思议的光辉映在她眼里。奸妇——我立即萌生这意念。同时,又好像很泄气,这计划的可怕,突然展现在我眼前。在此期间,那女人的淫乱,令人作呕的衰容,使我不断为之苦恼,这已无须再说,要是还能挽回,我真想当场收回前言。然后,羞辱那不贞的女人,把她推到耻辱的深渊。那样,即使我玩弄了她,说不定良心上还可以拿义愤当挡箭牌。但我还顾不上那样做。那女人宛如看透我的心思,忽然换了副表情,紧紧盯着我的眼睛——说老实话,我已骑虎难下,不得不同她约好杀渡的日子和时辰,因为我害怕,万一我反悔了,袈裟会向我报复。事至今日,这种惧怯之情仍死死揪着我的心。有人笑我胆小,就随他笑吧。因为他没看到袈裟当时的神情。“假若我不杀渡,看来即使袈裟不亲自动手,我也准会被她弄死的。与其那样,不如我把渡干掉的好。”——望着那女人无泪干哭的眼睛,我绝望地这么想。我发过誓后,看到袈裟苍白的脸上泛起酒窝一潭,俯首垂目在笑,岂不更加证实我的恐惧不是毫无来由的么?
唉,为了那可诅咒的约定,既不道德,又昧良心,现在还多了一重杀人的罪名。要是赶在今晚毁了约——这连我自己也不肯。一方面,我发过誓,而另一方面,我说过——是怕报复。这决不是欺骗。但除此之外,好像还有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呢?逼着我这个胆小鬼去杀一个无辜的男人,那巨大的力量到底来自何方?我不明白。我不知道,照理说——不,没这种事儿。我瞧不起那女人。我怕她。恨她。但即使如此,兴许还因为我爱那女人的缘故也未可知。
盛远还在徘徊蹀躞,已然不再做声。月光朗照。不知从何处传来时兴的歌声。
真个是人心非同无明之黑暗,好一似烦恼之火,命危夕旦……
下
夜晚,袈裟在帐子外,背着灯光,一边咬着袖子,陷入沉思之中。
独白
他究竟来不来呢?想必总不至于不来吧?月亮都快西斜了,可还没听见脚步声,他不会遽尔反悔吧。万一不来——唉,我又得像个妓女一样,抬起这张羞愧的脸,面对天日。我怎么会做出这种无耻事儿来的呢?那时,我与路旁的弃尸真毫无二致。受人侮辱,受人蹂躏,到头来落得厚着脸皮,丢人现眼,而且还得像哑巴一样,一声都不能言语。万一真是如此,纵然要死也死不了。不,他准会来。上次分手时,我盯住他的眼睛,心里没法不那么想。他怕我。尽管恨我,还瞧不起我,但却怕我。不错,要是就凭我自己,他未必肯答应来。可是,是我求他。算准了他的自私心理。不,是看透了他那自私自利引起的卑劣的恐怖。所以,我才能这么说。他准会悄悄来的,没错……
然而,单凭我自己,休想能办到。我这人有多惨呐。要是在三年前,就凭我的美貌,比什么都管用。说是三年前,不如说到那天为止,倒更接近真实也未可知。那天,在伯母家见到他时,我一眼就知自己的丑相印在了他的心上。他装得若无其事,像是在挑逗我,对我温声软语。但是一个女人,一旦得知自己丑陋,几句话怎能安慰得了。我只是觉得窝心,感到可怕,伤心难过。儿时,奶娘抱我看月蚀,感觉很可怕,但那时的心情比现在不知要强多少。我的种种梦想,顿时化为泡影。过后,仿佛细雨濛濛的黎明,凄凄惶惶的感觉一直围绕着我——我被这孤寂所震慑,如同死了一般,委身于他,委身于那个并不爱我、那个恨我瞧不起我的好色之徒——向他显示自己的丑陋,难道是因为耐不住那份孤寂?还是因为我的脸贴在他胸前,像给烧昏了一样,委时间把什么都搅糊涂了呢?要不,就是我跟他一样,被一种肮脏之心所驱使吧?这么想想,我都不好意思,感到害羞,无地自容。特别是离开他的臂弯,又复归自由之身时,我直觉得自己有多下贱呀!
气愤之情夹着凄凉之感,不管心里怎么想,千万不能哭,可眼泪还是止不往往下流。不过,这不仅是因为有亏妇道而备感悲伤。妇德有失,加之又遭轻贱,如癞皮狗一般,被人憎恶,受人虐待,这比什么都让我伤心。后来,我做了什么呢?现在想来,好像过去很久了,只模模糊糊记得一些。我抽泣之际,觉得他的胡子碰了我的耳朵,随着一股热鼻息,听到他低声对我说:“不是想杀渡吗?”听到这话,说来也奇怪,到现在也不明白,不知怎么当时心境一下豁亮起来。是兴奋么?如果说这时月光很明亮,恐怕是因为我心里高兴的缘故。总之,和明亮的月光不一样,那是一种兴致勃勃的心情。然而我从这句可怕的话里,岂不是感到一丝快慰么?唉,我这个女人呀,难道非要谋杀亲夫,还得照旧被人爱,才觉得痛快不成?
我好似这明亮的月夜,因为孤寂,因为心头一宽,又接着哭了一阵。接下来呢?然后呢?究竟是几时,诱使那人跟我约好来杀我丈夫这些事的?就在订约的那会儿,我才想起自己的丈夫。老实说,这还是头一回。在那之前,我一门心思只顾想自己的事,琢磨自己受人戏侮的事。只有在那时,才想到我丈夫,我那腼腆的丈夫——不,不能说是他的事。而是每当他要对我说什么时,总是微笑的面孔,清清楚楚呈现在我眼前。我的计策猛地兜上心来,恐怕也是忆起他那张面孔一瞬间的事。此言何出呢?因为当时我已决心一死了。能做出这样决定,岂不高兴。但是,当抬起这张哭脸,向那人望去时,便又像上次似的,看到自己的丑陋映在那人心上,喜悦之情顿时化为乌有。于是——又想起和奶娘一起看月蚀时黑沉沉的光景。恍如隐藏在喜悦的心情之下,形形色色的怪物都给放了出来似的。我要做丈夫的替身,难道真是因为爱他?不,不,在这好听的借口后面,是因为我曾委身他人,有一种赎罪的心情。可我没有自戕的勇气。我想在世人眼里,多少会显得好一些,我心里还存有这么一种卑劣的念头。何况这么做,八成还能得到宽恕。而我比这还要卑鄙,也更加丑陋。那人对我的憎恶、轻侮以及邪恶的情欲,我美其名曰做丈夫的替身,其实,不是想对这些个进行报复么?证据是,望着他的面孔,仿佛那月光一样,我的兴致忽然竟冰消瓦解,只有满腔的悲伤,转瞬间冻僵了我的心。我不是为丈夫去死,而是为了自己。我是因心灵受到伤害而感到愤然,身子受了玷污而为之悔恨,因这两个原因才去死的。唉,我活着毫无意义,而死也没有一点价值。
然而,我这没有价值的死法,比苟延残喘的活着,不知让人多开心哩。我忍住悲伤,强带欢颜,同他再三商订谋杀亲夫之约。可他也很敏感,从我的话语当中,也能听出一二,万一他失了约,恐怕也猜得出,清晨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既然如此,他誓也发过,是不会不来的。——那是风声吗?——一想到自从那天以来,一直痛苦忧伤,今夜总算熬到了头,心里顿觉一宽。明天,太阳想必会在我无头的尸体上,洒下一抹寒光吧。看到尸体,我丈夫——不,不要去想他,他是爱我的。可我对这爱却无能为力。很早以来,我就只爱一个男人。而这惟一的男人,今夜却要来杀我。在我看来,这灯台的光,也显得晶光耀眼。更不消说,我是被情人折磨致死的呢。
……袈裟吹灭了灯台的火,不大会儿,黑暗中隐约听到撬开板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线淡淡的月光泄了进来。
作者:芥川龙之介(1918年3月) 译者:艾莲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参考:
(故事摘自网络)日本古典史话《源平盛衰记》中有一则故事叫“湿发记”,读完很耐人寻味。
袈裟是渡左卫门的妻子,自幼被一个名叫盛远的男子所爱。他为她尝了许多相思之苦,最后忍耐不住了,便威胁袈裟的母亲,叫她一定设法叫袈裟回来同他幽会一次,否则便杀死她。袈裟的母亲无奈,只得托故将袈裟叫了回来,而且对她说明原因。袈裟为了母亲的生命,只好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满足了盛远的欲望。可是盛远得寸进尺,一心想与袈裟永久欢爱,便表示一定要杀死左卫门,并要求袈裟同谋。袈裟本是好女子,见到自己既失身于他,又如此相逼,知道这是孽债,不易摆脱,便自己打定主意,将计就计。她对盛远说,她回家后,要为丈夫洗发,并且用酒灌醉他。盛远来时,只要摸到湿发的头,便可下手。盛远信以为真,夜半摸到袈裟的家里,摸着睡在床上的一个湿发的头,便一刀割了下来。盛远满以为已经杀了袈裟的丈夫,十分高兴。可是回家一看,手中的人头竟是袈裟。
原来袈裟用酒灌醉了丈夫,自己却故意打湿了头发,睡在外床,一声不响地任随盛远杀了,了却这一段孽缘。
而在高慧勤女士的译作《蜘蛛之丝》(青岛出版社 2013年2月版)译序中,高提出了芥川“颠覆了《袈裟和盛远》女主人公历史上的‘烈女’形象,从另一侧面切入,具有偶像破坏的意味”。
个人理解,这个故事另起炉灶。一方面强调盛远虽然与袈裟肌肤相亲,却嫌恶她“姿色已衰”,觉得已经不再爱她了。出于凌辱她的目的,说出“要杀了渡”的话,而后又后悔说出这样的话,胆怯起来;另一方面袈裟三年来还深爱着盛远,但当她违背妇道,“耐不住孤寂”,与盛远发生关系时,却发现自己被他厌恶轻贱,愈发伤心。而当她听到盛远要谋杀渡,更觉得对不起丈夫,为了赎罪以及对盛远报复,她心生一计,决定做丈夫的替身,代替丈夫去死,这里和原来的故事很相像。所以文末写到:“太阳想必会在我无头的尸体上,洒下一抹寒光”。
至于故事的结局,“黑暗中隐约听到撬开门板的声音”,“一线淡淡的月光泄了进来”,看似开放含蓄,实则暗示了盛远的到来及袈裟悲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