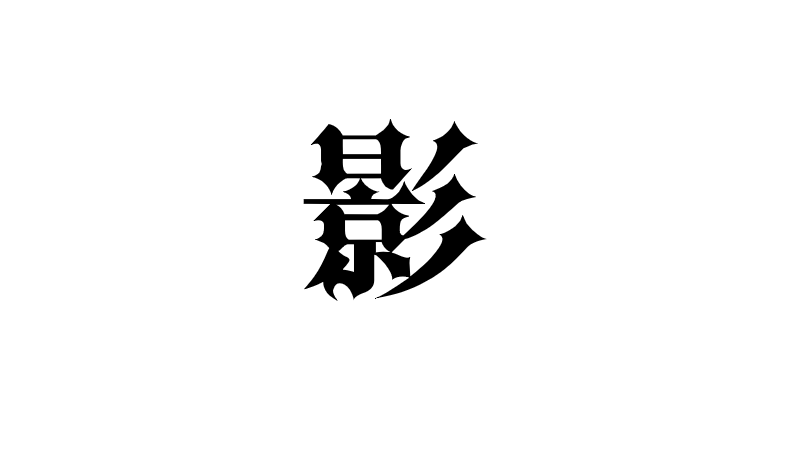
影
影
横滨
日华银行老板陈彩,今天也西装革履,伏案于成堆的商务文件间,叼着早已熄灭的烟卷,忙得错不开眼。残暑未消,寂寞充斥着垂着更纱窗帘的室内,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门散发着清漆的气味,只有对面传来打字机的轻微声响,时不时打破这片寂寞。小山高的文件处理完毕,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拿起桌上的电话,开腔竟是一口嗓音浑厚的日语:
“接到我家。”
“谁?阿婆吗?让夫人接下电话。房子吗?今晚我要去东京,嗯,晚上住那边。回不来,赶不上火车。你好好在家。什么?请医生来了吗?你肯定是神经衰弱了。行,挂了。”陈放下电话,不知为何面色忽然沉了下来,他用粗壮的手指划着火柴,终于点起一直叼着的烟,吸了起来。
……香烟的烟雾,花草的气味,刀叉与盘子碰撞的声音,从房间一角悠悠响起,与整体氛围格格不入的一首卡门。陈在一片吵闹中,双臂支桌,对着眼前的一杯啤酒不知所措。客人、服务生、换气扇,似乎都在转来转去,无不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只有那个柜台后的女子的面孔,让他无法错开目光。那女子看起来不过二十岁,额发烫成卷,施以薄薄的腮红,身着有些土气的磁青半襟,正背对着墙壁上贴着的镜子,忙不迭地用铅笔写着账单。
陈一气喝光这杯啤酒,不小的个头慢慢站起来,走向柜台。
“陈哥,什么时候给我买戒指?”女人说着,手里的笔也未曾停下。
“要等你手上戒指摘掉之后……”
陈一边从兜里摸着零钱,一边用下巴示意女子的手,那只手两年前开始,就已经戴上了一枚订婚戒指。
“那就今晚吧,你买给我。”女人突然拔下戒指,和啤酒一起推到陈的面前,“这可是我的护身符。”
咖啡馆外的柏油马路上,夏夜里一阵凉爽的风正吹过。陈站在路边,怔怔地仰望着星空。只有今夜,这些星星……
突然一阵敲门声,将陈拉回一年后的现实。
“请进。”
敲门声随即停止,清油味未消的门被打开,阴沉而苍白的今西书记无声地出现在门口。
“有您的信。”
陈只是略微颔首,脸上稍有对此外一言不发的今西的不满之意。今西仍然冷冷地奉上信件,行礼,依然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今西关上门后,陈掸了掸烟灰,拿起那封信。信封是普通的白色商用信封,上面是打字机打印的收件地址。本是没有任何不妥的一封信,可陈的表情不可抑制地充满了厌恶。
“又来了。”陈的粗眉皱起,嫌恶地“啧”了一声。然而他还是一头仰倒在转椅背上,双脚搭在桌沿,没用拆信刀,直接用手撕开了信封。
拜启
已再三敬告过阁下,尊夫人贞节有失。时至今日,如果您再不采取什么坚决的措施的话……
尊夫人每天和情夫厮混……房子夫人是日本人,做过咖啡店的女招待……您是中国人,在下不能坐视不管……如果之后不和夫人离婚,您会被万人耻笑……若有言语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您忠实的友人
敬上
陈依旧搭着桌子,就着蕾丝窗帘间泻入的夕照,细看那只女式金表。然而那表盖上刻的,却似乎不是房子的名字缩写。
“这是?”
“田中先生送的。你记得吧,经营仓库的——”婚后不久,房子站在衣柜前,朝着桌子一头的丈夫笑道。
桌上两个戒指盒,打开白天鹅绒的盖子来看,一枚是珍珠的,另一枚是土耳其玉的。
“是久米先生和野村先生给的。”
接着出现了珊瑚珠饰。
“很古典吧,是久保田先生送的。”
这种时候,陈就会像什么都不知道一般,静静地看着妻子的脸,若有所思地开口:
“这些可都是你的战利品。好好留着吧。”
被夕阳填满的房间里,房子再一次爽朗地笑了:
“也是你的战利品哟。”
当时他也很高兴,可现在……陈打了个寒噤,把搭在桌上的两条腿放了下来。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吓了他一跳。
“是我。好,让他跟我说。谁?我知道你这边是里见侦探所。你叫什么?吉井君,很好。有什么要报告的?来的人是谁?医生?那之后呢?也有可能。那你来一趟停车场吧。不,肯定能赶上最后一班火车。那到时见。”撂下听筒的陈彩,就像是安心了一般,静坐了一会儿。接着他一看见桌上女表的指针,按下了半自动的传唤铃。今西书记应声出现,从门后伸出半个瘦长的身子。
“今西君,跟郑君说,今晚代替我去东京出差。”陈的声音不知不觉间失去了一直以来的力度,今西仍然冷淡地行礼,关上门隐身而去。更纱窗帘外,夕阳西沉,薄暮渐浓,房间里蓦地染上一片赤色。一只不知从哪来的大苍蝇,带着低沉的振翅嗡嗡声,一圈圈地围着撑着头一动不动的陈,画着不规则的圆……
镰仓
夏末,时值黄昏,陈宅客房的蕾丝窗帘外,是不断蔓延的夕阳,如燃烧般盛开不衰的夹竹桃,给凉爽的房间带来一丝明快的色彩。房子坐在屋子一角的藤椅上,膝上伏着一只三花猫,略带愁容,目光游走在花间。
“老爷今晚在外留宿吗?”用人老妇在一旁的桌上摆好红茶茶具。
“是呀,今晚又是我一个人了。”
“如果您身体没问题的话,老仆我还能放心些——”
“今天山内医生说了,我的病就是神经过于疲乏,好好睡两天就会——欸?”
老妇也是一惊,看向房子,不知为何,房子孩子般的脸上,一双眼里充满恐惧。
“夫人,您怎么了?”
“嗯,没什么。不过……”房子强装镇定,扯出一点儿笑意,“刚刚窗边好像有人在偷看。”
可老妇到窗边查看之时,只有寂寥庭院中风中摇曳的夹竹桃和一望到底的草坪。
“啊啊,真讨厌,肯定是隔壁家的小孩子在恶作剧。”
房子想了想,最后慢慢说道:“不,不是隔壁家的小孩。我好像有印象——对对,上次和你一起去长谷的时候,后面好像一直跟着这么个年轻人,戴着鸭舌帽……不过也可能是我的错觉。”
“要真是那个男人的话怎么办呢?老爷也回不来,要不跟老头子或是警察讲讲吧。”
“哎呀,婆婆你太大惊小怪了。管他是谁,我一点儿都不怕。不过——不过要是真的是我的错觉——”老妪听到这里,疑惑地眨眨眼,“要真是错觉,我可能要就此疯掉也说不准啊。”
“夫人您就爱说笑。”老妇放下心来,微笑着收拾起茶具。
“不,婆婆你不知道。最近我一个人的时候,总觉得有谁站在我身后,就这样站着,盯着我……”房子沉浸在回忆中,神情迅速忧郁起来。
没有开灯的二楼卧室中,淡淡的香水味荡漾在昏暗之中。月亮升起,唯一的光源便是未曾放下窗帘的窗中,透进的模糊月光。房子沐浴在这微光之中,独自站在窗边,望着外面远处的松林。
今夜丈夫不会回来。用人们也都安置了。月夜下的庭院,只有风静静盘旋着。远处传来低微的钝响,那是海潮的声音。
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又出现了,有谁在身后窥视着自己。可除了她自己不可能有外人进来——不对,万一呢——不可能,睡前门都有好好落锁。那这种感觉到底——还是神经太过疲劳吧。她望向透着微光的松林,努力说服自己,可那种有谁在看着她的感觉,无论如何也无法消失,甚至越来越强烈。她鼓起勇气,胆战心惊地转身,卧室里果然没有别人,只有那只三花猫。果然是神经出了问题,才会产生这种错觉。可只一瞬,刚刚那种某种不知名的存在潜伏于这片黑暗中的感觉,马上又笼罩在房子的心头,那个难以名状的视线又一次盯上窗边房子的脸,房子从未感觉到如此难以忍受,她全身颤抖着伸出手,摸到离自己最近的那面墙上的电灯开关。灯亮的那一刻,一如往常的屋内陈设,覆盖了月光之下的晦暗不明,一切都回归到了可靠的现实之中。床、西式衣橱、盥洗台——如白昼般的光照之下,一切的一切,无比亲切地再次出现在眼前。自从一年前和陈结婚之后,所有的陈设未曾改变。在如此幸福的环境之中,无论怎样可怕的幻觉,都不过——
不。那怪异的存在,连这刺眼的灯光都不怕,盯着房子的视线竟然寸刻未离。房子双手掩面,失控大叫起来,可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此时心头的恐惧,已经超越了她有生以来的全部认知……一周前的记忆随着呼吸一点点倾泻出来。猫借机从她膝头跳下,顺滑齐整的背高高弓起,畅快地伸了个懒腰。
“谁都会出现那种错觉的。我家老头子修剪院子里的松树时,大白天的还以为听见了小孩子的笑声,那之后还跟我抱怨个不停,但他不也什么事都没有嘛。您不是也说,这种小事不值得费心思吗?”老妇拿起盛茶具的漆盆,像安慰孩子一般对她说。听到这里,房子的脸上也终于松快了些,有了笑意。
“肯定是隔壁的小孩在吓唬人。老头子也是胆子小,被那种事吓到。——啊,天已经这么晚了,老爷就这样住在那边也挺好。”
“洗澡水好了吗,婆婆?”
“准备好了,需要我帮您吗太太?”
“嗯,我马上去洗。”房子终于放松下来,从藤椅上起身。
“今晚隔壁的小孩也在放烟花呢。”
老妇跟在房子身后,静悄悄地关上门,只余已然看不清窗外夹竹桃的昏暗房间。可那只被二人遗忘的三花猫,就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一样,猛地扑到门口,又像贴着某人的脚蹭了过去。暮色笼罩的房间里,三花猫的双眼放出令人不安的磷光,目光所及之处,却空无一物……
横滨
日华洋行的值班室,昏暗的灯光下,书记今西蜷缩在长椅上,正在看一本杂志新刊。不久他便把杂志扔在一旁,小心翼翼地从里怀取出一张照片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那张苍白的脸,泛起一丝幸福的微笑。
那是陈彩的妻子房子,梳着裂桃髻的半身照。
镰仓
下行列车的汽笛响彻在星月夜空,陈彩将包对折夹在腋下,独自一人在检票口停下了脚步。站内一片寂静,昏暗的灯光下,坐在墙边长椅上的高个子男人,撑起一柄粗粗的藤杖起身,慢慢挪到陈彩身前,摘下宽沿鸭舌帽,用只有陈彩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陈先生吗?我是吉井。”
“今天辛苦了。”陈面无表情地盯着他说道。
“刚刚打过电话了——”
“那之后什么都没发生吗?”陈不容置疑地打断对方的那一刻,男子的下半句话就如同被生生崩飞。
“什么都没发生。大夫离开后,夫人一直和婆婆聊到天黑。接着沐浴用餐完毕,直到十点,一直在听收音机。”
“没有来什么客人吗?”
“没有,一位客人都没有。”
“你什么时候停止监视的?”
“十一点二十分。”吉井回答得很痛快。
“那之后到末班车之前,没有其他车次吧?”
“上行下行都没有。”
“嗯,今天谢谢你了。回去替我跟里见君带个好。”陈将草帽檐压低,看也不看脱帽致意的吉井,踩着站外的碎石大步走远。望着陈无所畏惧的背影,吉井不由得紧张地双肩紧绷。不过稍许他便放松下来,一边吹着口哨,拄着粗粗的藤杖,向停车场附近的旅店走去。
镰仓
一小时后,陈彩已经身在他们夫妇二人的卧室门口,做贼似的将耳朵贴在门上,动也不动地静听着。卧室外的走廊里,浓重的黑暗几乎压得人无法呼吸,其中微明一点,便是从卧室门锁孔漏出的些许灯光。陈压抑着跳得飞快几乎炸裂开来的心脏,耳朵严丝合缝地贴在门板上,全神贯注地听着门里的动静,然而门里却听不到任何交谈的声音,伴随这份寂静而来的,便是一股难以忍受的内疚之情。
从停车场回家的路上,他再一次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松枝笼罩的狭窄小径上,露水已经沾满了沙土。澄澈的夜空上无数星子的光芒,在松林的层层掩盖之下,投射在路上已所剩无几。可近海的潮风,却痛快地穿林而过,风声清晰可闻。陈独自一人,小心翼翼走在寂静的暗林之中,嗅着随风而来越发浓烈的松脂香气。
忽然陈停下了脚步,警惕地观察起不远的前方。前方几步远处,常年被常春藤覆盖的家宅砖墙周围,突然传来隐蔽的足音。不过再怎么仔细看,松林茂密遮掩,怎么也辨认不清。只是,一时间那足音并没有接近自己的方向,反倒好像移动到对面去了。
“想什么呢,又不是只有我才能在这条路上走。”陈腹诽着多疑的自己。可这条路唯一的通向应该只有自家内宅——就在这时,内门打开的声音随着海风而来,传进陈的耳朵里。
“真奇怪,早上的时候,内门还是锁着的。”一想到这里,陈彩就像寻到了猎物的猎犬,毫不犹豫地朝内门走去,可不知何时,内门早已再次落锁,怎么推也推不开。陈靠在门上,站在过膝的草丛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是我听错了吗?明明听到了门的声音……”与此同时,刚听到的脚步声,也彻底消失了。爬满常春藤的墙壁一头,陈宅早已灯火尽熄,矗立在星空之下。一股悲凉之情猛地冲向陈彩的心头,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悲从何来,冰冷的泪水,悄然从他脸上滑落,他就这样呆立在草丛中,听着单调的虫鸣。
“房子……”陈久违地呼唤起妻子的名字,如同在呻吟。
就在这时,高高的二层突然亮起灯来,照得人眼晕。
“那、那是——”陈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抓住手边最近的松枝,努力朝上看去。亮起灯的那间屋子——二层的卧室灯火通明,透过玻璃窗,屋内的一切清清楚楚。灯光浮在夜色里,攀上院墙内茂盛色松枝。接着,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出现在窗边,不巧的是,那人背对灯光,看不清他的面貌。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那是个男人的轮廓。陈紧紧抓着墙上的常春藤,努力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断断续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那封信——怎么可能,不是只有房子她——”陈彩立即翻过院墙,悄悄穿过院内的松树,在二层客房的窗户下藏好。窗下的夹竹桃已经被露水打湿了花叶……走廊一片黑暗中,满心嫉恨的陈彩咬着干裂的嘴唇,竖耳听着。果然,门里传来了一阵格外小心的脚步声,可又瞬间消失了。随即,关上窗户的声音显得格外尖锐,刺入神经高度紧张的陈的耳膜。
那之后又是漫长的寂静。在这片寂静里,脸色大变的陈,额角如同被榨木[1]挤榨过一般,淌满了冰冷的急汗。他哆嗦着去摸门把手,却发现门早已锁死。突然,屋内传来不知是梳子还是别针落地的声音,陈继续仔细听着,却没再听到拾起的声音。如此莫名其妙的声音,一点一点地击打着陈的心脏,他全身都在颤抖,只有耳朵仍然死死贴在门上。煎熬的数秒间,他已然紧张到极点,几近狂乱的视线不停地投向四周。这时,门的一端传来一声微弱的叹息。接着好像有人轻轻爬上了床。如果再多保持这个状态一分钟,陈可能就会在门口直接疯掉。
这时,门缝泻出细若蛛丝的朦胧光芒,如同天启一般照进他的眼里。陈猛地伏在地板上,贪婪地探向把手下的锁孔,向屋内看去——
刹那间,映入陈彩眼中的光景,是他一生也摆脱不了的,永远的诅咒……
横滨
书记今西将房子的照片放回里怀口袋,安静地从长椅上坐起。接着和往常一样,他一声不响地走进一片漆黑的隔壁房间。他按下电灯开关,四周立刻亮了起来。今西坐到桌前,台灯照亮了他面前的打字机,一双手敲敲打打,飞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不消多时,打字机便吐出一张印有几行字的白纸:
敬启
尊夫人贞节有失,恐怕已经无须在下多言。可您实在太过溺爱……
瞬间,今西的表情,完完全全是一张写满憎恶的面具。
镰仓
卧室的门已经大开。灯火通明下,床、衣橱、洗面池,都一如往常。陈彩呆立在房间一角,怔怔地看着床前的两人。一人是房子——倒不如说,到刚刚为止,她还能被叫作房子。而现在,这个曾经的“房子”,面色青紫,半吐着舌头,死死盯着天花板。另一个人是陈彩。和站在房间角落的陈彩分毫不差。那个陈彩压在房子身上,掐着她的脖子,双手手指几乎要陷进她的脖子里。他的头靠在房子裸露的胸前,不知生死。静默片刻,床上的那个陈彩,开始痛苦地喘息,他撑起笨重的身体,可刚一发力,马上又倒在床边的椅子上。
这时,房间一角的陈彩,沉默着走向那个“房子”,一双眼睛无限悲凉,望着她青紫的面孔。椅子上的陈彩,这时才意识到有其他人存在。他从椅子上跳起,充血的双眼里闪过阴冷的杀意。可待看清对方的一瞬间,他眼里的杀意,马上被难以言喻的恐惧代替:
“你是谁?!”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刚刚出现在松林里的,藏在后门的,还有在床边偷看的……是你……是你把我的妻子……把房子……”他中途噎住,又疯狂嘶吼起来。
“是你吧……你究竟,究竟是谁!”
另一个陈彩一言不发,他哀伤地看着对面的陈彩。而椅子前的陈彩,就像被这目光穿透,他睁大了狂乱的双眼,逐渐向墙壁一角瑟缩,嘴里还不停喃喃,“你是谁?是谁……”他跪在那个“房子”身边,缓缓地用手摩挲那纤细的脖颈,接着,他对着那残忍的指痕,吻了上去。一片光明却如同墓窖般寂静的卧室里,终于传出了断断续续的啜泣声。终于,墙角的陈彩和跪在地上的陈彩,一同掩面流泪起来……
东京
叫作《影》的电影放映完毕。我和一个女子,坐在活动影院的包厢里。
“刚才那片子应该都放完了吧。”
“你说哪部?”女子看向我,那忧郁的眼神,和电影中的房子如出一辙。
“刚刚的,叫作《影》的那个呀。”
女子没有多说,只是把手里的节目表递给我。不过,无论怎么找,都没有《影》这个名字。
“那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可又不记得自己睡着了,真奇怪。我给你讲讲这部片子吧……”我简单给她讲了讲故事梗概。
“这个片子我也有印象哦。”女子寂寞的眼底浮起一丝笑意,用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答道:
“我们,还是别在意什么影子了吧。”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0年7月) 译者:烧野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相关解读: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5297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