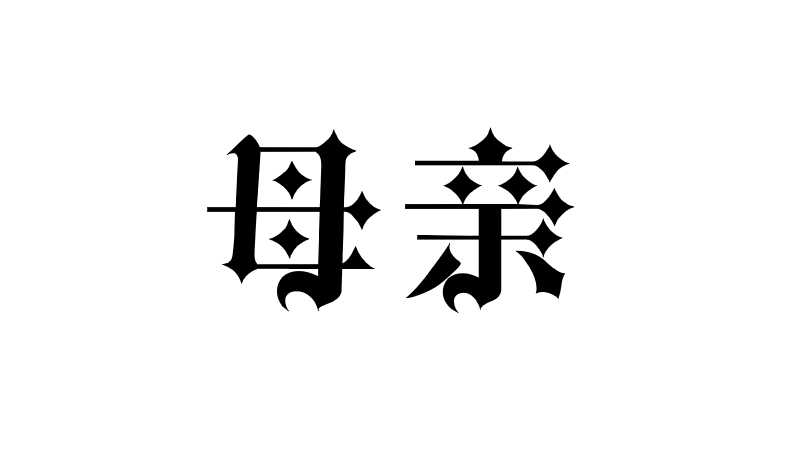
母亲
母亲
“是……是我的错吗?!那个孩子死了,是——”敏子突然又看向丈夫,她的眼神带着奇异的灼热,“那孩子死了,我高兴!可怜是可怜,但——但我高兴!高兴有错吗?!有错吗?!你说啊!”
一
西洋式的粉刷,和式的地席,上海特有的旅馆装潢从这二层的房间一隅可见一斑。首先进入视野的便是青空蓝的墙壁,接着是崭新的一张张地席,最后是梳着西式发型的女子——一切轮廓都在冰冷的光线中清晰地刻入视野。看女子的背影,她手里似乎正忙着什么针线活。披着有些土气的铭仙羽织的肩上,散落着从前额垂下的碎发,掩住苍白的面颊。薄薄的耳廓透着光,甚至掖在耳后的碎发也隐约可见。
外面还在下着雨,除了隔壁婴儿的啼哭声,整个房间保持着一片单调的静寂,甚至绵延不绝的雨声,也只是让这份单调更加深重。
“老公。”数分钟的沉默过后,女子淡淡地呼唤道,手里的活计却没停。
女子的丈夫身穿丹前羽织,远远地趴在一边,埋首于英文报纸。他似乎完全没听见妻子的呼唤,抬手掸了掸烟灰,没有抬眼。
“老公。”女子又叫了一声,这次她放下了针线。
“怎么了?”男子蓄着短须的嘴动了动,抬起他那活动家一般的圆滚滚的胖脑袋,显得有些不耐烦。
“这间房……这间房还能换吗?”
“换?咱们不是昨晚刚搬过来吗。”男子惊讶地看向妻子。
“是刚搬来……但是还是之前的那间更亮堂吧。”
男子想起那个采光极差的三层的房间,墙漆剥落、地席变色、垂着花棉布窗帘,窗前不知多久没浇水了的天竺葵上已经积了厚厚的尘埃,窗外始终脏乱的胡同里,总有戴着草帽的中国车夫,无所事事地闲逛,他顿感压抑起来。
“你不是不喜欢之前那间吗?”
“是,但,搬来这里之后一看,这里也不是很喜欢。”女子放下拿针的手,忧心忡忡地望向丈夫,她的眉头紧皱,那是一张眼角尖而长,透着某种锐利的面孔,可从那眼周一圈不自然的深色来看,这些年来她吃过的苦可想而知。就是这样一张略显病态的脸,即使在说一些稀松平常的事,也会显得格外激动。
“老公,再换一个吧?行不行?”
“但现在这间要比之前的亮堂得多,也宽敞得多,几乎无可挑剔……你到底哪里不满意呢?”
“也没什么特别不满意的地方……”女子答不上来,有些犹豫,可又鼓起勇气,重新央求丈夫,“就是不行吗?”
男子吹了吹报纸上散落的烟灰,不置可否。屋内再次回归静寂之中,窗外雨声仍未断绝。过了一会儿,男子仰面翻了个身躺倒,自言自语起来。
“春雨呀……”
“要是搬去芜湖,就写写俳句吧。”
女子并未接茬,重新开始手上的活计。
“芜湖那里要比你想象的好多了……首先员工宿舍都很大,院子也宽敞,里面花花草草也保养得很好,再怎么说那可是原来的雍家花园——”
男子突然噤了声,原本安静的房间里悄然响起啜泣的声音。
“敏子——”他唤住妻子,啜泣声随即止住片刻,又断断续续地传来。
“哎,敏子。”男子赶紧爬了起来,双肘交叠撑起半个身子,慌张地望向妻子。“咱们不是约好再也不抱怨了?别哭了呀,哎呀——”男子稍稍抬起眼,“是不是有什么不痛快?是不是想回日本了?不想待在中国,不想去乡下?”
“不,不是那样的。”敏子流着泪,意外地强行打断了丈夫,“你去哪,我就去哪,这一点我向来毫无怨言,但——”
敏子咬着下唇,紧闭双眼,想止住泪水。那苍白的面颊上,正燃起一股看不见的压迫感。颤抖的双肩,被泪水打湿的睫毛——男子望着妻子,这一瞬间,他没来由地被妻子的美丽所震撼。
“但……我就是不喜欢这间房子。”
“是呀,所以我刚刚就说,你是为什么讨厌呢?你得说出来,这样才——”
男子说着,发现敏子正盯着自己。妻子的泪水中闪现的,是混杂着敌意的悲哀。敏子到底为什么讨厌这间房子?男子不禁在心中发问,与此同时,敏子心里也想问丈夫同样的问题,自己为什么不喜欢这间房子?男子望着妻子,几次欲言又止,可当他刚把话咽回去,数秒之间,便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是因为那个呀……”男子似乎刻意在掩饰自己的动摇,干巴巴地说,“那个我也很在意。”
敏子听着,眼泪止不住地落到膝上。窗外,夕阳已被笼罩在雨幕之下,蓝色的粉墙对面,婴儿的哭声破开雨声,依旧源源不断地穿墙而来……
二
二楼的飘窗沐浴在朝阳的光辉中,对面的三层小楼背对日光,红砖上已生出薄薄一层青苔。若站在阴影里的走廊从飘窗向外看,就像在看一幅巨大的画,结实的槲木窗框,正像是画框一般镶在墙上。画正中间,正面向看客,织一只小小的足袋[1]。那女子要比敏子年轻些。雨后的日光格外明亮清澈,流淌在她披着华丽的大岛羽织的丰满肩头,些许反射在气色红润的脸上,就连唇上生着的细小绒毛,也透着细微的光。
中午十一点不到,这是旅馆一天之中最安静的时候。无论是做买卖的还是游客,抑或租客,这个时候大抵都外出了。住在这里打工的,自然不到半夜是回不来的,长长的走廊里,只有女佣的脚步声偶尔回荡其间。
这时,远处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位四十上下的女佣端着红茶茶具,从飘窗对着的走廊走来,如同皮影一般在画中出现。要是女子不出声,那女佣可能根本不会发觉,就这样经过。
“阿清?”
女佣闻声,稍稍颔首招呼,退回飘窗的方向:
“哎哟,真是不得闲——小少爷呢?”
“我们家的小少爷?正睡着呢。”女子停下织针,露出孩子般的笑容,“阿清啊,其实有的时候吧……”
“怎么了?看您一脸严肃。”日光直射在女佣的围裙上,黑眼珠被照得透亮,带着笑意。
“隔壁的野村夫人……是姓野村吧,那位夫人?”
“是呀,野村敏子夫人。”
“敏子夫人?那和我同名呢。他们家已经离开了吗?”
“没有,大约还要再停留五六日。这之后,似乎是要到芜湖去……”
“但我之前经过,隔壁好像已经没人了。”
“是,因为昨晚突然换到三层去了。”
“原来如此。”女子似乎想起什么,轻轻偏过圆圆的面庞,“就是她吧,一到这里就失去孩子的那位。”
“是呀,真可怜,虽然当时马上就送医院了。”
“原来孩子是在医院没的,怪不得我这什么都不知道。”女子除去刘海儿的眉间略有一丝忧郁神色,然而不消片刻,快活的微笑又回到了她的脸上,她开玩笑似的给女佣使眼色:
“好啦,我都知道了,你可以走啦。”
“您可真过分。”女佣不由得笑了起来,“虽然您这么无情,但老宅来电话的话,我还是会向老爷保密的。”
“好呀,不过你还是快走吧,一会儿红茶都凉了哦。”
女佣离开了,飘窗前,女子重新拿起织针,小声哼起歌来。
中午十一点不到,这时旅馆一天之中最安静的时候。这段时间,女佣会把每个房间里枯萎了的花收拾掉,小厮会把二楼三楼黄铜的楼梯扶手擦得亮晶晶。不断蔓延的沉默之中,只有外面的嘈杂声伴随阳光,一同从一扇扇玻璃窗透进来。这时,一个毛线球从女子膝头滚落,红色的线球弹了三弹,扯线到了走廊里,接着不知是谁经过,悄悄地把它捡了起来。
“多谢。”女子赶紧从椅子上起身,尴尬地道谢,一看那捡起毛线球的人,竟是刚刚和人聊起的,隔壁那位瘦削的夫人。
“没关系。”毛线球从干瘦的手里,让渡到白若凝脂的指尖,“这里真暖和呀。”敏子眯起眼睛,向飘窗的方向走去。
“是呀,这么坐着就教人犯困。”两位母亲看着对方,微笑起来。
“哎呀,这小袜子多可爱!”敏子的声音略显刺耳,女子听了不自觉地稍稍错开目光。
“我都两年没动过织针了,最近也是太闲了。”
“我就算有空,也全都用来偷懒啦。”
女子无奈地笑笑,将手里的织物撂在藤椅上。敏子无心的话,让她略受打击。
“您家的小少爷——是小少爷吧,什么时候出生的呀?”敏子一手抚着头发,偷眼瞧着女子,她实在好奇昨天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啼哭的来源。然而她心里也明明白白,这个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同时也会增添新的伤痛。就像小动物在眼镜蛇面前,被催眠了一般一动不敢动,敏子的心,也已经被苦痛侵蚀得麻木了,又像是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贪图一时之快,总是忍不住揭开伤口去看的自伤冲动,这也是敏子的一种病态心理。
“今年正月出生的。”女子试探着回答,而一看敏子的神情,心里又过意不去起来。
“您家里的事我听说了。”
“嗯,是因为肺炎,现在想想就像做梦一样啊。”敏子泪水上涌,勉强笑道。
“您搬得急,也没能好生安慰。”女子也眼泛泪光,“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
“当时是难过极了,不过现在也无可奈何了。”
两位母亲静立着,寂寥地望向窗外的朝阳。
“最近恶性流感闹得很凶,还是老家更好呢,气候什么的也比这里要好——”女子沉吟片刻,忽然说道,“您刚搬来可能不了解,这边经常下大雨呢,今年尤其——啊,孩子哭了。”女子侧耳倾听,脸上马上露出笑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好意思,失陪一下。”
话音未落,刚刚的女佣抱着哭泣的婴儿,穿着草鞋“嗒嗒”地走过来。那婴儿穿着绉绸的小和服,小脸纠纠巴巴,肉乎乎的小下巴——如此健康的孩子!敏子第一反应便是想逃离。
“我正擦窗户呢,小少爷就醒了。”
“不好意思呀。”女子驾轻就熟地将婴儿接过抱在胸前。
“哎呀,真可爱。”敏子凑近去瞧,婴儿身上的奶味有些刺鼻。
“噢——噢——胖了不少哟……”女子的精神越发抖擞起来,脸上是难掩的笑意。女子并非不同情敏子,只是——只是,那乳房之中,饱胀的、母亲的乳房之中,汪然满溢的得意之情,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
三
雍家花园的槐与柳,在午后的风中摇摆,搅得日光在庭院的草木土地间撒下破碎的影子。一张在整个庭院中略显突兀的水色吊床挂在树间,一个身量圆润的男子,只穿着一身夏季西装,也躺在一吊床的破碎光影之中。他点起一根香烟,望着槐树枝上挂着的中国式鸟笼。笼里的大约是文鸟,也在或明或暗的光斑之中,绕着笼中横木上蹿下跳,时不时不可思议地望向男人。男人笑着把烟叼在嘴里,对着鸟笼念叨着“喂”“怎么着”逗趣儿,就像在和人聊天。摇曳的庭木之中,有淡淡的草木香蒸腾而出。一声汽船的笛鸣,远远地从天际传来,除此之外便再无其他声响。那汽船应该早已远去,向西或向东,划开红浊的长江水,带起层层令人目眩的水脉。码头上,几乎一丝不挂的乞丐正嚼着西瓜皮,一旁一群小猪崽正排成长长一排挤在横卧着的母猪身侧,争着抢着吃奶……男子厌倦了逗鸟,陷入这般空想之中,不知不觉就要睡去……
“老公。”
男子睁大了双眼。站在吊床一旁的敏子,脸色已经远远好于在上海旅馆的时候。她的发髻、腰带、中形纹样的浴衣、敷着白粉的面孔,同样沐浴在细碎的光斑之中。男子一见妻子,舒舒服服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接着不耐烦地从吊床上坐起身子。
“有你的信。”敏子笑着递给他几个信封,同时,自己也从桃色浴衣的内襟,抽出一张粉红色的信封,取出一张小小的信纸,“也有我的信呢。”
男子撑着身子,嚼着烟屁股,大大咧咧地读起信来,敏子也站着仔细读起那粉色的信纸。
此时,安详的夫妻二人,头顶仍是槐柳洒下的破碎光影。文鸟也几乎不作声,只有一只嗡嗡叫的小虫萦绕在男子肩头,又直直飞了下去……片刻沉默过后,敏子突然睁大双眼,叫出了声:
“天哪,隔壁的婴儿死掉了!”
“隔壁的?”男子稍稍有些在意。
“就是,哎呀,就是住在上海旅馆的时候……”
“啊啊,那家吗?真可怜哪。”
“那孩子明明那么健康……”
“因为什么?生病了吗?”
“嗯,就是流感。说是一开始只是以为孩子受凉了……”敏子读着信,越说越激动,“‘送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又是打针又是吸氧的,什么手段都使了——然后’,然后,哇,这上怎么说的——啊,哭声,‘哭声越来越小,夜里快到十一点零五的时候,终于咽了气,其时我心中的悲痛,您定能体会……’”
“可怜哪。”男子念叨着相同的话,晃晃悠悠地躺回去。听着妻子念信,此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那个濒死的婴孩,他小小的嘴里,艰难地喘着气……不知何时,那细弱的喘息声又变成了哭声,夹杂在雨声里的,健康婴儿的哭声——
“‘……您定能体会,总是想起当时和您的交谈,您当时想必也——啊啊,我也不想活下去了。’”
敏子的眼里充满忧郁,神经质地皱起眉头,突然沉默了,接着,看到笼子里的文鸟,开心地拍起一双纤细滋润的手。
“我有个好主意!我们把那文鸟放了吧!”
“放了?你不是最喜欢这只鸟了吗?”
“喜欢也没办法,就当为那孩子超度了,就当是放生了,对吧?放了它,它也会高兴的——我好像够不着,你帮我拿下来吧。”敏子走到槐树根底下踮起穿着气垫草鞋的脚,使劲伸长胳膊去够,但是鸟笼挂得太高,很难够到。文鸟受了惊,扑棱小膀子乱飞,饵盒里的黍米撒了一地。男子看着拔脖挺胸,努力踮脚的妻子,顿觉好笑。
“就是够不着,够不着。”敏子猛地转身对丈夫说,“帮我拿下来,帮帮我。”
“你肯定够不着哇,要是踩个什么东西去够那还两说——想放也不急于这一时吧。”
“我现在就想放了它。帮我拿下来吧,要是不帮我我可就使坏了噢?把你吊床拆下来——”
敏子盯着他,可眼里嘴角,都荡漾着笑意。那是一种彻底失去平静的、强烈的幸福的笑容。男子看着妻子的微笑,不知怎的感到一丝冷酷,那种熟悉的寒意,似乎来自那些平日里隐匿于日光炙烤之下的草木深处,窥视人类的不知名力量。
“别傻了——”男子扔掉烟头,半开玩笑地喝止妻子,“无论如何,那个夫人死了孩子,咱们在这里笑闹就不应该……”
听到这里,敏子的脸色陡然苍白起来。她像个闹脾气的孩子,长长的睫毛低垂,一言不发地撕起那封信来。男子的脸垮了一下,或许是为了避免尴尬,又马上快活地接话下去。
“不过,这一切也都是命数哇。可能在上海的时候身体就不好了,送进医院又着急,不送医院又担心——”
男子忽然噤了声,敏子正盯着自己的脚尖,脸被笼罩在阴影之中,已然出现泪痕。男子不知如何是好,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过后,敏子的脸色变得极差,转过头不去看丈夫。
“怎么了?”
“是……是我的错吗?!那个孩子死了,是——”敏子突然又看向丈夫,她的眼神带着奇异的灼热,“那孩子死了,我高兴!可怜是可怜,但——但我高兴!高兴有错吗?!有错吗?!你说啊!”
敏子的声音从未像此时一样,紧绷着一股狂暴的力量。此时,男子已全身暴露在正午炫目的日光里,一种人力远不能及的森然,正紧紧压迫在他的胸口,令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1年8月) 译者:烧野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