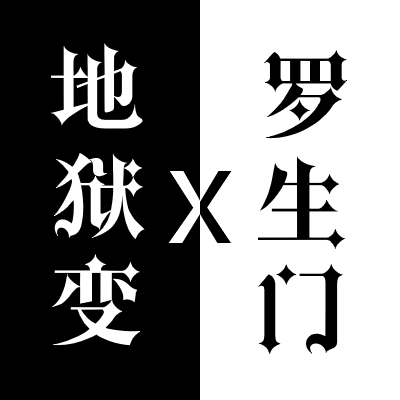庭院
庭院
上
这是名叫中村的豪门世家的庭院,过去曾经是高官显宦外出巡游时的驿站旅馆。
在明治维新后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庭院好歹总算是维持着旧态原貌、葫芦瓢形状的池塘仍然澄静清澈,而石山上的松枝也照旧低垂多姿。栖鹤轩、洗心亭——这些楼台亭榭也依然如故。在池塘尽头的后山崖上,一条银白色的瀑布飞流而下。当年,和宫殿下下巡时不吝题名的石灯笼,如今仍旧伫立在一片棠棣花中。这些棠棣花年复一年地向四周蔓延开来。可是,在这庭院的某个地方却弥漫着一种无法隐藏的荒芜感。特别是初春时节——当庭院内外的树梢上同时萌发娇嫩的新叶时,更是会让人感觉到:在这明媚的人工景色背后,有某种令人不安的野蛮力量正一步步进逼而来。
中村家的老头子,乃是一个生性豪爽侠义之人,如今隐居在家,颐养天年。他在面对庭院的正堂里向炉而坐,与头上长着疥疮的老伴忽而下棋,忽而玩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管如此,有时候当老伴连续赢了五六盘棋之后,他就会较上劲来,甚至勃然大怒。继承家业的长子与表妹才新婚不久,住在一间独立开来但又与走廊相连的狭窄房屋里。这个老大以文室为雅号,是一个性情暴烈之人。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兄弟昆仲自不用说,就连老头子也不得不对他退避三分。惟独当时寄居在这家旅馆里的乞丐师傅井月,经常到他房中来闲玩。奇怪的是,长子也偏偏只对井月又是敬酒,又是央求他挥笔题字,显得好不高兴。“山间尚有花香在,又闻杜鹃声声鸣。井月。无处不是好景致,飞流依稀更撩人。文室。”——这样的吟和之作也还好端端地保留着。说来,老大还有两个弟弟——老二做了一个身为米店老板的姻亲的养子,老三则在一家离镇上有五六里远的大型酒坊里做工。就像是有约在先似的,他们俩都很少回老家来。因为老三不仅住得很远,而且原本就和当家的老大性情不合。老二则因为放荡不羁,落得个身败名裂,以至于连养父母的家也鲜为造访。
在这两三年里,庭院史是愈发荒芜得厉害了。只见池塘里开始漂浮起绿藻,而灌木从里也夹杂起枯树来了。不久,隐居的老人也在某个久旱无雨的酷夏,因脑溢血而猝然死亡。在暴卒的四五天之前,老头子喝着喝着烧洒,竟然看见一位周身白装的古代公卿好几次出入于池塘对面的洗心亭。至少在他眼里,自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目睹了那样的幻象。翌年的暮春,老二卷走了养父母家的钱财,与一个小酒馆的女招待一道私奔了。而就在同年的秋天,老大的妻子生下了一个不足月的男婴。
父亲死后,老大与母亲一起住在了正堂里。而老大腾出来的那间下房,则租借给了当地的小学校长。因为校长信奉福泽谕吉[1]的功利主义学说,所以,不知几何时说服了老大,让他在庭院里也种上了果树。如此一来,每当春天来临,在庭院里那些司空见惯的松树和柳枝之间,又有桃花、杏花和李花竞相绽放,显得五颜六色,缤纷耀眼。校长常常和老大一起,一边踯躅在新的果树园里,一边不无感慨地说道:“这样一来,还可以好好地赏花呐。真可谓一举两得。”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假山和池塘,还有亭榭,与过去相比,就更是显得毫不起眼,大有不久于世的感觉了。换言之,除了自然本身的荒芜之外,人为的破坏也在加剧着它的荒芜。
是年秋天,后山上又发生了近年罕有的山林火灾。从那以后,泻入池塘的瀑布使陡然断绝了水源。谁知祸不单行,在雪花初降的时节,当家的老大又患上了疾病。经大夫诊断,说他染上的是那种从前叫做痨病,而今叫做肺病的疾患。老大每天躺躺坐坐,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了。第二年的正月,他和回家来拜年的老三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以至于把手炉一古脑儿向对方猛掷过去。老三从此一去不返,即使在大哥奄奄一息之时也不曾回来见上一面。一年多以后,老大在妻子的彻夜陪伴中,躺在蚊帐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但闻青蛙鸣。可井月啊,你又身在何方?”——这就是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然而,或许是对这一带的风景已经看腻了吧,井月甚至连讨饭化缘也不肯再来此地了。
老大的周年忌一过,老三就和东家的小女儿结了婚。所幸的是,恰好原本借住下房的小学校长调任其他地方了,这才让老三得以和新娘住了进来。他们把漆得乌黑发亮的衣橱搬进下房,还装饰了红白二色的锦缎。谁知在正堂里,老大的妻子又犯了病。而且,犯的是和丈夫同样的痨病,老大撇下的独苗——廉一也只好在母亲咯血后,每晚与祖母睡在一起。祖母在上床睡觉之前,必定会把手巾搭在自己的头上。尽管如此,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老鼠就会寻着头上疥疮的臭气,悄悄靠近过来。不用说,有时候一旦忘记了罩一层手巾,头部便会遭到老鼠的咬噬。在同年的岁末,老大的妻子就如同一盏耗尽的油灯一般,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在出殡下葬后的第二天,假山背后的栖鹤轩就在一场大雪中坍塌了。
当下一个春天再度造访之时,庭院里只有位于浑浊池塘边的杂树林出现了少许的变化:在残留着洗心亭茅草屋顶的杂树丛中,娇嫩的新芽正萌发出来。
中
在一个雪压冬云的阴霾黄昏,离家出走达十年之久的老二又重新回到了父亲的家中。所谓父亲的家——实际上已经无异于老三的家了。对老二的归来,老三既没有流露出特别不快的神情,也没有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总之,就像是什么也不曾发生一样,平静地将浪子二哥迎入家门。
从此,染有麻风病的老二就一直守着被炉,躺在正屋的佛堂里了。在佛堂的巨大佛龛里,并排祭放着父亲和长兄的灵牌。他紧紧拉上佛龛的隔扇,以免看见那些灵牌。再说,除了一同共进三餐,他几乎从不和母亲、弟弟及弟媳见面。唯有身为孤儿的廉一常常到他的起居室里来玩耍。老二总是在廉一的纸制石板上给他画上一些山呀船呀之类的东西。“向岛正值花烂漫,啊,茶房的阿姐,请你出来一会儿吧!”——有时候,老二还会用潦草的字迹写下这样一些从前的小调。
不久,又到了春天。庭院里草木与日俱长,日渐稀疏的桃树和杏树则夹杂在草木当中开起花来。而洗心亭的影子也倒映在了水色黯然的池面上。可老二却依旧兀自蜷缩在佛堂里足不出户,即便在大白天,也是昏昏欲睡,神思恍惚。有一天,他的耳畔隐约传来了三弦琴微弱的乐音。与此同时,还开始听见断断续续的歌声。“此番諏訪之战,身为松本之亲信,吉江为加固炮阵,义不容辞奔赴疆场,……”老二就那样躺着,微微抬起头来。是的,那歌声和琴声无疑全都来自于身在饭厅的母亲。“那日他一身戎装,光耀四射,侠义豪气,威猛英武;啊,勇士吉江,仪表堂堂……”或许是唱给孙儿听吧,母亲继续吟唱着重新填词的大津绘小调[2],说来,这还是二三十年前的流行小曲,是生性风流的老头子从当地某个名妓那儿学来的。“吉江他身饮敌弹,捐躯丰桥,命如草露,倏然消殒,然而英雄美名,万世流芳……”听着听着,老二那张满是胡须的脸上,不知何时竟熠熠闪光。
那以后又过去了两三天,老三在长满款冬的假山背后,看见了正在掘土的哥哥。老二气喘吁吁地挥动着不听使唤的铁锹,那模样让人觉得颇为滑稽,但其中又包含着某种认真的劲头。“哥哥,你在干吗?”——老三嘴里叼着香烟,从背后向老二搭讪道。“是问我吗?”——老二眯缝着眼睛,恍若有些刺眼似的抬头望着弟弟。“想在这儿开挖一条小溪呐。”“开挖小溪来干吗?”“我想让庭院恢复原来的模样。”——老三只是嗤嗤地笑着,再也没有继续追问了。
老二每天都扛着铁锹,继续拼命地挖掘小溪。对于病魔缠身的他来说,就是这点活儿也够他折腾的了。首先,他很容易疲劳,再则,又是一种生疏的劳作,所以,他的手上磨出了老茧,指甲也发生了断裂,干起活来老是不顺。有时候他甚至撂下铁锹,像死人一般就地横躺着,一动也不动。仿佛无论时间如何流逝,他的周围都—成不变:升腾的阳气笼罩着庭院,红花绿叶交相辉映。但是,当时间在静谧中过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执拗地挥动起铁锹来了。
然而,数日之后,庭院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显著的变化。池塘里照旧野草从生,而灌木林中的杂树也是枝繁叶茂。特别是在果树的花瓣凋零之后,让人觉得比以前更加荒凉。不仅如此,全家老小没有一个人对老二的计划表示同情理解。喜欢投机冒险的老三成天醉心于大米的行情和蚕丝投机。老三的妻子对老二的病情抱着一种出自女人本能的厌恶。母亲也——考虑到老二的身体状况,母亲也害怕,过多地鼓捣泥土会有损他的健康。尽管如此,老二还是一意孤行,不顾人们和自然的冷酷,一点一点地改造着庭院。
不久后一个雨过天晴的早晨,他走到庭院里一看,只见在款冬垂悬着的小溪边上,廉一正朝上面堆砌着石头。“叔叔!”——廉一兴高采烈地仰起头来望着他。“从今天起,就让我也来当个帮手吧!”“唔,那就拜托了。”老二的脸上此刻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笑容。从那以后,廉一哪儿也不去,一心意地给二叔当起了帮手。——为了犒劳侄子,当两个人在树阴下小憩时,老二就会告诉廉一好些他所不知道的新鲜事儿,什么大海呀,东京呀,还有铁路等等。廉一一边啃着青梅,一边就像是被人施了催眠术似的,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
这一年的梅雨期却是一个干旱无雨的季节。他们——日益衰老而又病魔缠身的老二和童子廉一,不顾酷烈的阳光和青草的热气,挖土掘池,砍树伐木,使整个工程大有进展。千方百计总算是克服了外界的障碍,可来自内部因素的阻碍却让人一筹莫展。老二虽然能够在大脑的幻象中重现往昔庭院的整体轮廓,可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细节,比如树木的配置、幽径的安排等等,他的记忆就变得依稀模糊了。他常常在工作正酣的时候,突然拄着铁锹,怔怔地环顾着周遭。“怎么啦?”——这种时候,廉一必定会朝二叔的脸上投去不安的目光。“这儿过去是什么样儿的啊?”满身是汗的老二在原地不停地转悠着,嘴里一个劲儿地嘟哝着,“这棵枫树原本好像不是在这儿的呐。”而旁边的廉一则只好用沾满泥土的手来捏死蚂蚁。
内在因素的阻碍并不仅限于此。渐渐地,随着夏季一天盛似一天,或许是因为过于疲劳吧,老二的神经开始出现了混乱。一度挖好的池塘又被他掩埋起来,拔掉了松树的地方又被他重新栽上了松树——诸如此类的事件也屡屡发生。尤其让廉一生气的是,为了打池桩,他竟然把水边的一株柳树砍掉了。“这株柳树不是前几天才刚刚栽下的吗?”——廉一瞪大眼睛盯着叔叔说道。“是吗?我不知怎的,就是记不得了。”——老二一副忧郁的眼神,注视着烈日下的池塘。
尽管如此,当秋天到来的时候,一座庭院在草木丛中朦朦胧胧地浮现出来了。与过去相比,不用说,既没有栖鹤轩,也没有瀑布飞泉。不,过去那种出自著名庭院大师之手的优雅情趣,几乎无处可寻。但是,那儿的确出现了一座“庭院”。池塘再次用清澈见底的水面来映照出圆形的假山。而松树也重新在洗心亭前面悠然地舒展起枝叶。可是,就在庭院复兴的同时,老二却卧床不起了。不仅每天高烧不止,而且周身的骨节也阵阵作痛。“这都是因为过于疲劳所至。”——母亲坐在儿子的枕畔,反复唠叨着同样的怨言。但老二却备感幸福。不用说,庭院里还有许多需要修茸的地方,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总之,没有白干一场。——对此他感到心满意足。十年的辛劳让他学会了达观,而这种达观又转而拯救了他。
深秋时节,老二在谁也没有留意的情况下,静悄悄地告别了人世。而发现他已经死去的人,乃是廉一。他一边大声地哭嚎着,一边朝紧挨走廊的下房飞奔而去。全家人无不带着一张惊愕的面孔,聚集到了死者的周围。“瞧,哥哥他像是在笑着呐。”——老一回过头看着母亲说道。“哇,今天佛像前的隔扇是打开着的呐。”——老三的妻子看也不看死人,而只是留心着佛龛说道。
在埋葬了老二之后,廉一常常独自一人端坐在洗心亭里,一筹莫展似的凝望着晚秋的池水和树木……
下
这是一个名叫中村的豪门世家的庭院,曾经是达官显宦们外出巡游的驿站旅馆。它在一度复兴之后,过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如今又整个儿遭到了破坏。在备受毁损的遗迹上,业已建起了一座车站,而在车站的前面,又耸立起了一家小小的餐馆。
眼下,中村的老家已经不再有任何人留在那里了。当然,老母亲也早已跻身于死者的行列了,老三在事业遭到重创之后,据说是去了大阪。
火车每天都在车站上停靠,然后又离开车站扬长而去。车站上,一个年轻的站长正独自伏案工作着。他在完成闲散事务的间歇里,时而眺望着青青的山脉,时而与当地的站务员进行闲聊。但即便在他们的谈话中,也不曾提到过中村家的逸闻。谁也不曾想到过,如今他们身在的地方曾经有过假山和亭榭。不过,在此期间,廉一却在东京赤坂的一间西洋画研究所里,对着画架挥笔作画。从天窗流泻进来的光线、油画颜料所发出的气味,还有盘成桃髻的模特儿女郎——研究所的氛围和故乡老家的氛围简直是大相径庭,但是,当廉一挥动画笔时,心里却常常浮现出一张老人的面孔。那张面孔一边微笑着,一边对因连续创作而筋疲力尽的廉一说道:“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就曾经帮过我。现在轮到我来帮你了。”……
廉一如今仍旧忍受着贫困,每天坚持绘画,从不辍笔。而至于老三的消息,那就无人知晓了。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2年6月) 译者:杨伟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