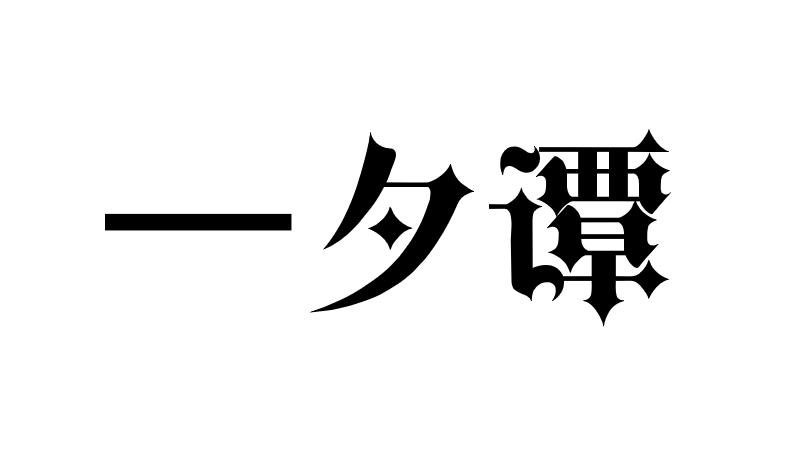
一夕谭
一夕谭
“总之,如今这个年月,对人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哟。因为就连和田这样的人也和艺妓有交道呐。”
名叫藤井的律师在喝完一杯老酒之后,有些小题大做地环顾着大家的脸。围坐在圆桌旁边的我们,是曾经寄宿在同一个学生宿舍里的六个中年人。聚会的地点是在日比谷陶陶亭的二楼上,而时间则是在六月的某个雨夜。——不用说,藤井发表这一通言论的时候,我们大家的脸上都已经浮现出了醉意。
“实际上,当我无意中看见那家伙的时候,确实有一种不胜今昔之感……”藤井津津有味地继续说道,“在大伙管他叫‘医科生和田’时,他还是一个柔道选手,一名讨伐学校炊事员[1]的大将,一个崇拜利文斯敦[2]的狂热分子,一个在数九寒天里也只穿一件单衣的男人——总而言之,堪称典型的英雄豪杰呗。可是,现在就连你,也和艺妓打起了交道。而且是和柳桥那个名叫小缘的艺妓……”
“莫非这阵子你又改换了码头?”
突然从旁边杀出这声冷枪来的,乃是名叫饭沼的银行支店长。
“改换了码头?为什么?”
“和田结识那个艺妓,恐怕就是在你带他去那儿的时候吧?”
“你可不要胡乱猜测。谁会带和田去那种地方呢?”藤井气宇轩昂地扬起眉头,说道,“那是在上个月的几号呢?反正是一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吧。与久违的和田碰头之后,他说,我们还是到浅草去吧。虽然对浅草也没什么兴趣,可既然是老朋友提出的建议,我也就顺从地表示了首肯。于是,两个人在大晌午就出发去了六区……”
“然后一起去看了场电影,对吧?”这次是我抢过话头来猜测道。
“如果是看场电影那倒敢情好,可实际上,是去坐了旋转木马呐。说来,当时我们俩还一本正经地骑在了木马上。即便现在想来,也觉得那样怪愚蠢的,可这也不是我的主意呀。只因为和田太想坐了,所以,仅仅是为了奉陪他,我才一起坐了上去的。——不过,那玩意儿坐起来倒也并不轻松。特别是像野口那样胃上有毛病的人,还是免坐为好啦。”
名叫野口的大学教授正吃着青蓝色的松花皮蛋,所以,只是在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但藤井毫不在乎,不时地用目光扫视着和田,洋洋得意地继续说道:
“和田乘坐的是白色的木马,而我乘坐的乃是红色的木马。当木马伴随着乐队的演奏旋转开来的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直犯嘀咕,不知会怎么样呐。只感觉到屁股腾空,两眼昏花,唯一的想法就是千万别在晃荡中甩下马去。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发现——在栏杆外面的观众当中,夹杂着一个艺妓模样的女人。一个脸色苍白,眼睛湿润,渗透着某种忧郁感的女人······”
“哪怕只是看清了你所描述的情景,不也说明你是好端端的吗?还说什么两眼昏花,真是奇怪!”饭沼又一次插嘴道。“所以我不是才特意加上了一句‘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吗?只见眼前站着一个楚楚动人的女人,头上当然是梳着那种银杏叶形状的发型啦,身上穿着淡蓝色的条纹哔叽衣服,还系着一条印花布的腰带,就恍若那些出现在花柳小说插图中的女人一般。这时,你猜那女人怎么着了?只见她瞅了一眼我的脸,然后露出了嫣然一笑。我甚至来不及惊讶,就从她面前一掠而过了,因为我正坐在木马上呗。就在我寻思着她是谁的当口,乐队的那帮人已经赫然出现在了我乘坐的红色木马跟前……”
我们全都笑了起来。
“第二次也一样。那女人又露出了嫣然的微笑,随即便很快消失了。然后就只剩下了木马和马车还在来回旋转着,上腾下跃,要不就只能听见嘟嘟鸣叫的号声,或是咚咚作响的鼓声了。——我不由得感慨万分:这不就是人生的象征吗?我们全都被迫坐在现实生活的木马上,即使偶尔邂逅了‘幸福‘,可还来不及捕捉住它,便已经与它失之交臂了。倘若试图捕捉住’幸福’,那就索性从木马上跳将下去好啦。”
“你恐怕不会真的翻身下马吧?”带着讥讽口吻说这话的,是一个名叫木村的、某电器公司的总工程师。
“玩笑是千万开不得的。哲学归哲学,人生归人生。——不过,就在这样思忖着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那女人的微笑了。这时,我才无意中发现——实际上我也为自己的发现大吃了一惊——遗憾的是,那女人的微笑并不是冲着我来的。而是冲着那个讨伐食堂炊事员的大将、崇拜利文斯敦的狂人分子,即医生和田良平的。”
“不过,没有按照哲学翻身下马,或许算是唯一的侥幸吧。”就连沉默寡言的野口也忍不住开了一句玩笑。
但藤并却依旧执拗地继续说道:
“只要木马一转到那女人面前,和田这家伙就会兴高采烈地朝她点头行礼。他躬身坐在白色的木马上,唯有领带在胸前左右翻飞。”
“你胡说!”
和田也终于打破了沉默。他刚才一直苦笑着,大口大口地啜饮着老酒。
“什么?怎么会是胡说呢?——不过,那还算是好的。一旦走出旋转木马的场地,和旧就像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一样,只顾着和女人一个劲儿地聊天。而那女人也口口声声地管他叫‘先生先生’的。惟独我就像是一个多余的角色……”
“哇,这倒的确是个难得的趣闻。”饭沼一边把银匙伸进偌大的鱼翅汤碗里,一边回头看着旁边的和田说道,“喂,你听我说,这样看来,今天晚上的会费就只能请你帮我代付了。”
“说什么蠢话!那女人乃是一个朋友的小妾呢。”
和田拄着两只手肘,态度生硬地说道。他的脸看上去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加黝黑。眼睛和鼻子也长得与普通的都市人相去甚远。而且,他那剃成中分发型的脑袋,就如同岩石一般结实。记得过去参加某场校际比赛时,他在左肘骨折的情况下,竟然还打翻了五个对手。—即便现在他穿着黑色的西服和条纹的裤子,一身当今的流行装束,可在某个地方却仍旧栩栩如生地保留着当时的英雄风范。
“饭沼!那是不是你包养的小妾?”
藤井歪着头注视着对方,随即又露出了那种洒醉后的嗤笑。
“或许吧。”饭沼冷冷地搪塞了一句,然后再次回过头瞅了瞅和田,“是谁呀?你所说的那个朋友。”
“一个叫做若槻的实业家——我们当中难道没有人知道他吗?从庆应什么的毕业以后,如今就职于自己的银行。年龄嘛,也和我们相差无几。他长着白净的肤色,一双柔和的眼睛,还留着短短的胡须。——总而言之,是一个酷爱风流的好男人吧。”
“就是若槻峰太郎,俳号叫青盖,对吧?”
我从一旁插嘴道。说起那个名叫若槻的实业家,其实四五天之前,我还和他一道看过一场戏呐。
“是的,还出版过一本名叫《青盖句集》的书。——而他就是小缘的主人呗。不,准确地说,直到两个月之前,都还是她的主人。不过。眼下倒是已经断绝了关系……”
“嘿——这么说来,那个叫做若槻的人······”
“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窗。”
“这可是越来越精彩了。”藤井又一次发出了兴奋的声音。
“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你居然和所谓的中学同窗一起到处拈花惹草。”
“你胡说什么呀!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还是在进入大学附属医院之后。当时受若槻的拜托,给她帮了点小忙。我记得,好像是蓄脓症之类的手术……”说着,和田一口气喝干了一杯老酒。随即两只眼睛开始闪烁起深邃的光芒,“不过,那女人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家伙呐。”
“迷上她了?”木村平静地揶揄道。
“可能是迷上了她吧。也可能一点也没有迷上。不过,此刻我更想讲述的,乃是她和若槻的关系……”
和田在做出了这样的铺垫之后,用他不曾有过的雄辩口吻开始讲道:
“就像藤井说的那样,前不久我的确是偶然地碰到了小缘。但见面后一摆谈才知道,小缘两个月之前已经与若槻分手了。我问了问分手的原因,她也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回答,只是凄寂地笑着说了一句:我原本就不是他那样的风流雅士嘛。
“当时我也没有深究,就那样与她告别了。谁知昨天——昨天下午,不是下雨了吗?就在雨下得正酣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若槻的信,邀请我一起外出共进晚餐。恰好我也正闲着,所以,就提前出了门,先到若槻家里去看了看。只见他正呆在宽敞的书斋里优哉游哉地看着书。而我呢,尽管是一个野蛮人,对风流之道一窍不通,但一走进若槻的书斋,也不禁感触良深:原来所谓的艺术性,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啊!首先,无论什么时候去,神龛里都总是悬着挂轴,也从不间断地供奉着鲜花。至于他家里的藏书嘛,除了装满日本书籍的箱子以外,还有总是陈列着西洋书籍的书橱。并且,在豪华的桌子旁边,有时还摆放着一把三弦琴。而若槻自己也身在其中,一副恍若当代浮世绘中那种通达之人的模样。昨天他也穿的是一身奇妙的衣服,所以,我忍不住问了问那是什么,结果他回答说,是什么运动衫。尽管我的朋友很多,但穿所谓运动衫的人,除了若槻,恐怕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吧。——说起他的生活,大体就是这个样子吧。
“那天吃饭时,我一边和若槻举杯畅饮,一边听他讲述自己与小缘之间的恩恩怨怨。原来是小缘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不过,这或许也没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原以为对方会是怎样一个男人呐,结果据说只是一个摆弄三弦琴的下三流说唱艺人。听到这些,你们也会忍不住嘲笑小缘的愚蠢吧。可实际上,当时的我甚至就连苦笑都做不到。
“你们当然无从知道了,事实上,这三年来,小缘简直是给若槻添尽了麻烦。不光小缘的母亲,还有她的妹妹,都一直承蒙若槻的关照。而且,就说小缘自己吧,若槻不仅教她读书写字,还让她学歌习舞,凡是她喜欢的,全都让她悉数掌握。所以,在舞蹈方面,小缘终于得到师傅的恩准,取上了自己的艺名,而在演唱长谣方面也成了柳桥首屈一指的名角。除此之外,据说她不仅能作俳句,还是千荫流派的书法高手。这些都多亏了若槻。既然你们都觉得荒唐至极,更何况知道这一切的我了,又怎能不瞠目结舌呢?
“若槻这样对我说道:‘其实,与那女人分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过,在培养那女人这一点上,我倒确实是尽了自己的所能。我一直抱着这样一个希望,就是要把她培养成一个对所有事物都不乏理解的、兴趣广泛的女人。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次才更是备感失望。倘若真是想找个男人,也不至于找那么一个说唱艺人吧。尽管她在学习琴棋书画上是那么努力,可骨子里的粗鄙本性却压根儿没有改变——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就会涌起——股苦涩的情愫……’
“若槻还这样说道:‘近半年来,或许那女人是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吧。有一阵子,她几乎每天都念叨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三弦琴了。一边说着,还一边像个孩子似的哭泣着。我问她,这又是为什么呢,谁知她竟罗列出一大通莫名其妙的道理,说我其实并不喜欢她,而之所以强迫她学歌习舞,其原因就在于此。那种时候,无论我说什么,她都没有半点要听的意思。只是不胜委屈地一直重复着一句话,说我冷酷无情。不过,一旦发作完了,这些又都变成了笑话……’
“若槻还这样说道:“据说那弹三弦琴的说唱艺人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粗野之人,以前曾与同一个烤鸡店的女佣相好,当那女佣有了别的男人时,他到处殴打那个女佣,直到把对方打得遍体鳞伤。除此之外,还听说过那男人的种种轶事,比如他故意殉情自杀,还与师傅的女儿一起私奔等等。竟然迷恋上那样的男人,小缘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不能不为小缘的堕落而瞠目结舌。但在倾听若槻讲述的过程中,不知为什么,牵动着我心灵的,竟然是对小缘的同情。诚然,作为小缘的主人,若槻或许堪称当世罕见的通达之人。但他不是说了,与那个女人分手,并不觉得有什么吗?即便那只是一种外交辞令,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他对她并没有什么狂烈而执著的爱恋。狂烈而执著的爱恋——比如,那个说唱艺人不是因为憎恨女人的薄情,而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吗?比起优雅而冷淡的若槻,倒是虽然粗俗但却狂烈的说唱艺人更让人痴迷——如果站在小缘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小缘说,若槻让她学歌习舞,乃是对她没有爱情的证据。即使从这句话中,我看到的也不只是歇斯底里。小缘显然知道,在自己与若槻之间毕竟有着一道鸿沟。
“然而,我也无意祝福小缘,祝福她和说唱艺人的结合。或许很难断言,他们会幸福还是不幸吧。——但倘若真的会不幸,我想,遭到诅咒的,也不该是那个男人,而是迫使小缘走上这条道路的通达之人若槻青盖。若槻——不,准确地说,是当世所有的通达之人,如果仅仅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人来看,无疑都是值得爱戴的人物吧。他们既熟知芭蕉[3],也深谙列奥·托尔斯泰。既了解池大雅[4],也懂得武者小路实笃。还懂得卡尔·马克思。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不知道热烈的爱情,不知道创造所带来的巨大喜悦,也不知道疯狂的道德热情。对狂烈的事物——就是将地球变得庄严肃穆的狂烈事物——一无所知。我想,正是在这儿,既有着他们的致命伤,也潜藏着他们的危害性。其危害之一,就是会主动出击,把其他人也变成通达之人;其危害之二,就是恰恰相反,将其他人变得更加粗俗。小缘这样的人不就是例证吗?自古以来,口干舌燥者,即便是看见泥泞之水,不也会张口痛饮吗?倘若小缘没有当过若槻的小妾,或许反倒不会和说唱艺人成为相好吧。
“倘若他们会幸福,——不,哪怕仅仅是用说唱艺人来取代了若槻,其幸福也就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吧。刚才藤井不是说了吗?我们全都坐在现实生活的木马上,所以,即使偶尔邂逅了‘幸福’,也来不及捕捉住它,便已经与它失之交臂了。倘若真的试图捕捉住那种‘幸福’,那就索性翻身下马好啦。——换句话说,小缘就是毅然而然地从现实生活的木马上跳了下来。那种狂烈的喜悦和痛苦,绝不是若槻这样的通达之人所能了解的东西。一想到人生的价值,即便对一百个若槻吐以唾沫,也会对一个小缘表示自己的敬意吧。你们不这么认为吗?”
和田那双带着醉意的眼睛闪烁着熠熠的光芒,环视着周围鸦雀无声的几个人。但藤井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脑袋耷拉在圆桌上,酣然进入了梦乡。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2年6月) 译者:杨伟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