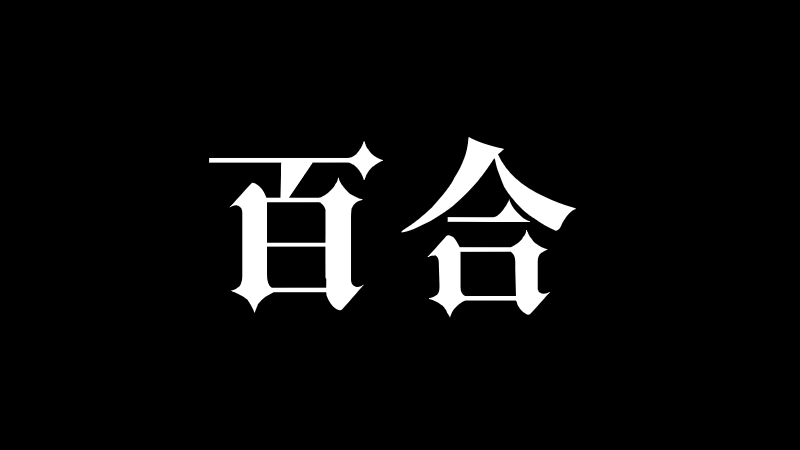
百合
百合
良平在某个杂志社里当校对员。不过,这并非他的初衷。所以,只要有一丁点闲暇,他也会出神地阅读日文版的马克思著作。要不,就一边用粗大的指头鼓捣着Colden Bat牌的廉价香烟,一边憧憬着俄罗斯。而每当这种时候,关于百合的往事,也会蓦然掠过他的心间,化作无数断断续续回忆中的某一个片段。
今年七岁的良平,此刻正在自个家的厨房里,大口地吃着有些为时过早的午饭。这时,隔壁家的金三一脸油光闪亮的汗珠,活像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一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径直跑到厨房里的洗碗池旁边,说道:
“喂,阿良,刚才——就是在刚才,我发现了一株连体百合呢。”
为了强调是一株连体百合,金三还特意把两根食指并在一起,举到上翘着的鼻子尖上给良平看。
“是并在一起的连体百合吗?”
良平不由得瞠目结舌。要知道,从同一个根部上长出两株百合,这可是很稀奇的。
“哎,那可是两株又粗又大的百合呢,长得就像人的小雀雀,而且,颜色还是红的……”
金三一边用松开的衣带头子揩拭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如痴如醉地说道。受到这番话的感染,良平也不知不觉地撂下碗筷,挨着他在洗碗池旁边蹲了下来。
“快把饭吃完吧!管它是连体的也罢,是红色的也罢。”
母亲在隔壁宽敞的客厅里剪切着养蚕的桑叶,对着良平叮嘱了两三次。但他就像是压根儿没有听见一样,连珠炮似的向金三发问道:百合的芽儿究竟有多粗?两株芽儿是不是一样长?当然,金三也回答得气宇轩昂:两株芽儿就跟大拇指一样粗,长度当然也恰好相同。这样的百合就是寻遍整个世界,恐怕也找不着吧……
“喂,阿良,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说着,金三有些狡黠地瞅了瞅良平的母亲,然后悄悄拽了拽良平的衣角。去看那并在一起、颜色又红、而且还像人的小雀雀一样的连体百合——没有比这更大的诱惑了。良平来不及回答,就匆匆地套上了母亲的草鞋。可草鞋不仅很潮润,鞋带也有些太松了。
“良平!——瞧你!饭还没有吃完就……”
母亲发出了又惊又气的声音。不料,这时的良平已经赶在头里,穿过了背后的庭园。走出后院,只见小路的对面有着一片迷蒙的灌木丛,其间长满了初生的嫩芽。良平正要朝那个方向拐过去,谁知金三一边大叫着“不对,是这边呐”,一边向有着农田的右前方跑了过去。而良平这时已经跨出了一大步。只见他夸张地掉过头,猫着腰转身回跑。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如果不摆出这种架势,就很难涌起那种威风凛凛的感觉。
“什么,原来是在农田的土堤上呀?”
“嗯,是在农田中间呐。就是在这对面的麦田里……”
一说完,金三就躬身钻进了栽满桑树的田埂上。在桑树那纵横交错的枝头上,已经抽满了三厘米大小的、十字纹路的嫩叶。良平也从树枝间一穿而过,紧紧尾随在金三的背后。在他的鼻子尖跟前,是金三那打着补丁的屁股。只见金三那松开的衣带正随风飘荡着。
穿过那片桑田,终于看见了长出秸秆的麦田。金三依旧跑在前面,沿着被桑树和麦秸夹在中间的田埂,再次朝右侧拐了过去。而就在这时,身手敏捷的良平一下子超过了金三。可不等他跑出五六米远,金三便发出怒气冲冲的话音,迫使他停住了脚步。
“你这是干什么呀?明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有些扫兴的良平,只好不情愿地让金三走在头里。这时,两个人都已经停止了奔跑,只是默默无言地向前走着,听凭麦秸与自己的身体相互摩挲。但刚一走到麦田角落里那修着土堤的地方,金三突然对着良平露出了笑脸,用手指了指脚下的田埂。
“瞧,就是这儿了。”
听他这么一说,良平也不由得把不快抛在了脑后。
“哪个?哪个?”
他佝身打量着田埂。就像金三所说的那样,两株带着红叶的百合,正高昂着它们富有光泽的头颅。即便已经听人说过,但亲眼目睹这百合的美丽,依旧会惊讶得目瞪口呆。
“喂,该是很粗,对吧?”
金三得意洋洋地看着良平。良平只是点了点头,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百合的新芽。
“喂,该是很粗,对吧?”
金三又追问了一次,然后试图伸出手去触摸右面的那株新芽。这时,良平就像是如梦初醒一般,慌忙挡开了金三的手。
“哎,别动它!要不,会碰断的。”
“摸一摸有什么呢?又不是你的百合!”
金三又生气了。可这一次良平也毫不示弱。
“可也不是你的呀。”
“不是我的,摸一摸又有什么呢?”
“我说了叫你住手!因为会碰断的!”
“才不会断呐!我刚才就使劲摸过它了。”
既然说刚才都已经使劲摸过,那良平也就只好默不作声了。金三就那样蹲在那里,比刚才更加粗暴地摆弄着百合的嫩芽。尽管如此,不足三寸长的新芽却岿然不动。
“那么,我也摸摸看吧!”
良平终于放下心来,一边窥探着金三的脸色,一边轻轻地摸了摸左边的新芽。红色的嫩芽给良平的指尖带来了一种奇妙的踏实感,使他从那种触觉中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慰。
“真棒!”
良平兀自微笑了。过了一会儿,金三突然开口说道:
“既然新芽发得这么好,就像人的小雀雀一样,那么,想必下面的球根也很大吧。——喂,阿良,要不要挖出来瞧瞧?”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已经将手指插进了田埂的泥土中。这次,良平所受到的惊吓远远超过了刚才。
“快住手吧!我说,让你快住手!”然后,良平又小声地说道,“要是给谁看见了,你准会被骂死的!”
生长在农田里的百合不同于那些荒山野岭里的百合。除了农田的主人,谁也不准擅自掘取——这一点金三也心知肚明。他有些依依不舍地在百合四周的泥土上画了个圆圈,然后老老实实地听从了良平的劝诫。
在晴朗天空的某个地方,一直响彻着云雀的鸣叫。两个小男孩就在这美妙的声音下面,一边爱抚着连体百合,一边郑重其事地相互约定:其一,关于这株百合,决不告诉任何其他伙伴;其二,每天早晨去学校之前,两个人一起来看望百合……
第二天早晨,就像约定的那样,两个人结伴来到了长着百合的麦田边。只见百合那红色的芽尖上还残留着晶莹的露珠。于是,金三负责右侧的新芽,而良平则负责左面的新芽,分别用手指弹掉了上面的露珠。
“真粗啊!”
今天早晨,良平又一次陶醉在百合新芽的壮观中。
“这样看来,它该有五年了吧。”
“你说五年?!……”金三朝良平的脸上投去充满轻蔑的目光,说道,“才五年?!恐怕该有十年左右了吧。”
“十年?!如果说有十年,那不是比我年龄还大吗?”
“是呀。当然比你年龄大啦。”
“那么说来,也就该开十朵花吧?”
五年的百合开五朵花,十年的百合开十朵花——几何时,他们曾从长辈那儿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是啊,当然要开十朵花呀。”金三用庄严的口吻说道。
良平内心有些踌躇,嘴上却带着辩解的语气嘟哝道:
“早点开就好了。”
“怎么会开呢?又不是夏天。”金三又一次奚落着良平。
“是夏天开吗?怎么会呢?应该是在下雨的季节吧?”
“下雨的季节,不就是夏天吗?”
“夏天应该是穿白色和服的时候呐。”良平决不肯轻易服输,说道,“下雨的季节,怎么会是夏天呢?”
“傻瓜!穿白色和服,不就是在伏天吗?”
“胡说!不信,你去问我娘!穿白色的和服,就是在夏天嘛!”
话音未落,良平的左脸颊已经挨了金三的一拳。但就在挨揍的同时,他也给了对方狠狠一击。
“你太自以为是了!”
脸色骤变的金三,用尽力气把良平向后一推,良平顿时仰面跌倒在麦田的田埂上。因为田埂上打着露水,所以,他的脸和衣服全都粘上了烂泥。尽管如此,他还是飞身跳将起来,冷不防抱住了金三。或许是因为遭到突然袭击吧,很少败阵的金三,这时候也跌了个屁股蹲儿。而且他摔倒的地方恰好紧挨着百合。
“如果想打架,那就过来吧!在那儿会伤着百合的,往这边来吧!”
金三高昂着下巴,纵身跳到了长着桑树的田埂上。良平也只好哭丧着脸,跟着转移到那边的田埂上。于是,两个人又 开始扭揪在一起。满脸通红的金三抓住良平的前襟,前后左右地推搡着。平时,要是被人这样折腾,良平早就号啕大哭了,但这天早晨,他却没有哭。不仅如此,即使脑袋开始晕眩,他也照样顽强地扭住对方,决不松手。
这时,突然有人从桑树中间探出了头来。
“喂,你们在打架呀?”
两个人终于停止了扭揪。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脸上有着浅浅麻窝的农家妇女。她是一个名叫惣吉的校友的母亲。或许是来采摘桑叶的吧,只见她穿着睡衣,把布手巾罩在头上,怀里抱着一个竹篓。她用审视的目光来回打量着两个男孩。
“是在进行相扑比赛呐,阿姨。”
金一故意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说道,但良平却一边战抖着,一边打断了他的话:
“他撒谎!明明是在打架!”
“你才是撒谎呐!”
金三一把抓住了良平的耳朵。但幸运的是,不等他使劲拽拉,惣吉的母亲便带着可怕的表情,走过来一下子扳开了他的手。
“你总是这么粗暴,不讲道理。不久前,把我们家惣吉的额头打了个伤口的,也是你吧。”
看见金三被人训斥,良平真想说一句:“活该!”但不等他说出口来,不知为何,他的眼眶里竟盈满了泪水。就在这时,金三一下子甩开惣吉母亲的手,用单脚蹦跳着,穿过一棵棵桑树,一边朝对面逃跑而去,一边大声喊叫道:
“日金山上天阴了!良平的眼睛下雨了!”
第二天,从拂晓时便下起了春天里罕见的大雨。良平家因为没有给蚕子储备足够的桑叶,所以一到正午,他的父母就掸掉蓑衣上的灰尘,找出很旧没用的草帽,开始匆忙地做起了出门采桑的准备。但即便在这种时候,良平也只是一边咀嚼着肉桂皮儿,一边满脑子想着百合的事情。雨下得这么大,没准百合的嫩芽已经被打断了吧?没准和田里的泥土一起,被连根带芽地冲走了吧?……
“金三这家伙,也肯定很担心吧?”
良平又转念想到了金三。这想法让他自己也觉得怪可笑的。其实,金三的家就在隔壁,只要沿着屋檐走过去,甚至连雨伞也不用撑呐。但是,一想到昨天的那场风波,他就打消了去找金三的念头。良平琢磨着,即使对方主动来找自己,开始也千万不要搭理他。如此一来,那家伙也就肯定会垂头丧气的吧。……(未完)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2年9月) 译者:唐先容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