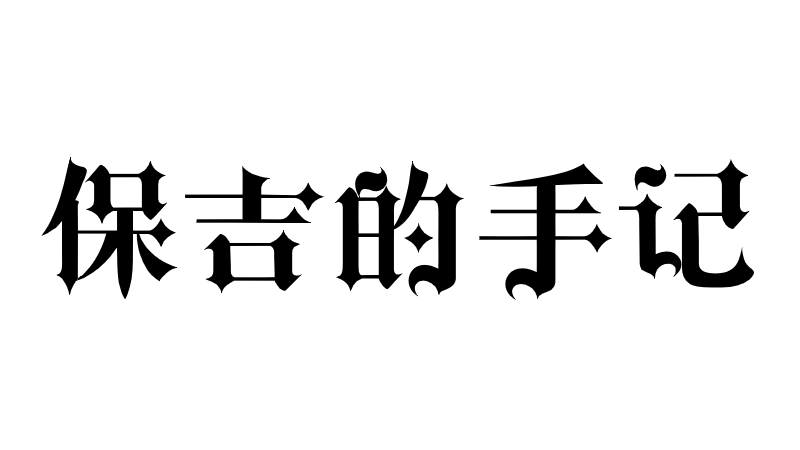
保吉的手记
保吉的手记
汪!
一个冬日的黄昏,保吉在一家算不得干净的餐馆二楼上嚼着油腥臭的烤面包。而在他就座的桌子前面,是一堵业已裂纹毕生的白色墙壁。而且,那儿还贴着一张细长的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另有ホッ卜(热)三明治供应”。(保吉的一个同事曾把它读作“呵——热三明治”,一本正经地感到不可思议过。)字条的左侧是一道下楼的阶梯,右侧则紧挨着一扇玻璃窗户。他一边嚼着烤面包,一边不时茫然地眺望着窗户的外面。在窗外的马路对面,有一家白铁皮屋顶的旧衣铺,只见店堂里悬挂着好些蓝色的工作服和黄褐色的斗篷。
那天晚上,从六点半开始,学校里要举行英语演讲会。保吉也自然有义务出席该会。只因不住在这个镇上,所以,从放学后到六点半的这段时间里,哪怕打心眼里不情愿,他也只能蜷缩在这个地方。想来,土歧哀果[1]就写过这样的和歌——如果记忆有误,就只好敬请包涵了——“千里来此地,牛排乏味如嚼蜡,岂不恋吾妻。”保吉每次来到这儿,就必定会想起这首和歌。只是他还不曾结婚,谈不上有那样一个令他爱恋的妻子。然而,当他望着旧衣铺的店堂,嘴里啃着ホット(热)三明治时,那“岂不恋吾妻”的诗句就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嘴唇。
这时保吉注意到,在自己身后有两个年轻的海军武官正啜饮着啤酒。其中的一个他也认识,是同一所学校的会计官。保吉平素与武官疏于往来,所以,自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不,不仅限于名字,就连他的军衔是属于少尉,还是属于中尉,也一概不知。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每个月去领月饷时,钱必定会经过这个武官之手,而另一个顾客那就全然不认识了。每当那两个人倾杯而尽,又重新追加啤酒时,嘴上尽足嚷嚷着“来酒啊!”“喂!”之类的语句。尽管如此,女侍依旧不厌其烦地用两手捧着酒杯,不亦乐乎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而对于保吉这边,即便只是要一杯红茶,也老是不肯轻易地送将过来。说来,这也不是此家餐馆特有的现象。在这个镇上,无论去到哪一家咖啡馆和餐馆,无一不是这样一副德行。
那两个人一边呷着啤酒,一边大声地说着什么。当然,保吉并非有意要偷听他们的谈话。但蓦然间,一句话却让保吉大吃了一惊:“叫一声‘汪’!”保吉是一个对狗没有好感的人。一想到在不喜欢狗的文学家中间,可以列举出歌德和斯特林堡的名字,他就会感到一阵欣慰。因此,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的,是这种地方惯常豢养的那种大洋犬。与此同时,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攫住了他,就恍若那种狗正在他的身后窜来窜去似的。
他不由得偷觑了一下身后。幸好没有看见狗的影子。惟有那个会计官一面望着窗外,一面嗤嗤地笑着,保吉由此推测到,或许狗就在窗户的外面吧。但不知为什么,却又总感到有些蹊跷。这时,会计官又一次开口说道:“叫一声‘汪’!喂,快叫啊!”保吉稍微扭过身子,窥探着对面的窗下。首先映入他视线的,是那些兼做正宗名酒广告的门灯,它们悬垂在屋檐下,此刻还没有点亮。然后看见的是卷起来的遮阳帘子。随后是晒在用啤酒桶做的太平水桶上而忘记了拾掇的木屐罩。接着出现的是马路上的水凼。再接下来——直到最后,都没有看见狗的影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乞丐。只见他兀自伫立在那儿,抬头仰望着二楼的窗户,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
“叫一声‘汪’!莫非你不肯叫?”
会计官又在这样对乞丐呼叫道。在他的这句话语里,似乎有着某种能够控制乞丐心灵的力量。乞丐几乎就像是一个梦游症患者一般,眼睛依旧朝上望着,而身体则向着窗户挪近了一两步。保吉这才终于明白了那个坏心眼的会计官的恶作剧。恶作剧?——或许不是什么恶作剧吧。否则,便堪称一种实验。是对人为了消除口腹之饥,到底肯在多大程度上牺牲自己尊严的实验。在保吉看来,这个问题大可不必像现在这样来进行什么实验。以扫[2]为了烤肉而放弃了长子的权利,保吉也是为了面包而做了一名教书匠的。只要看看这样一些事实,不就足矣吗?可是,对于那个实验心理学者来说,仅凭这些,是很难满足其研究心理的吧。正如今天自己教授给学生们的那句拉丁文所言:“嗜癖无可理喻。”人各有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倘若想实验一番,那就随其所便好了。——保吉就这样一边思忖着,一边望着窗下的乞丐。
会计官沉默了一阵子。于是,乞丐开始忐忑不安地张望着马路的前后左右。显然,即便对仿效狗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感,但乞丐肯定还是觉得,周遭人们的耳目令人生畏。谁知不等乞丐定下神来,会计官就把一张通红的脸伸出了窗外,这一次只见他手里挥舞着什么东西,嘴上还说道:
“叫一声‘汪’!如果你肯叫,我就给你这个!”
有那么一刹那,乞丐的脸上似乎燃烧起了求食的欲望。保吉时常会对乞丐这种人物萌发一种罗曼蒂克的兴趣,而一次也不曾涌起过类似于怜悯或同情的感觉。倘若有人说他自己有过那种感觉,保吉肯定会认为,说这话的人要么是一个傻瓜,要么就是在撒谎。但此刻,当看见那个小乞丐仰着头,双目生辉的模样,他的心里不免萌生了一丝怜爱。不过,这里所用的“一丝”这个词,的确堪称不折不扣的“一丝”。与其说保吉觉得那小乞丐值得怜爱,不如说他从那乞丐的身影中欣赏到了一种伦勃朗[3]式的艺术效果。
“不愿叫?喂,快叫一声‘汪’啊!”
乞丐紧蹙起眉头,叫了一声:
“汪!”
但声音委实太过微弱。
“再大声一点!”
“汪!汪!”
乞丐终于吠叫了两声。不等声音落地,一只脐橙便戛然向窗外扔了下去。——接下来的事情大家肯定不难设想了。不用说,乞丐朝着脐橙来了个饿狼扑食,自然引得会计官哈哈大笑。
那以后过去了一个星期,又到了发饷的日子。保吉到会计部门那里领取月饷,只见那个会计官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忽而翻弄那边的账簿,忽而摊开这边的文件。看见保吉进来,他只说了一句:“是来领月饷的吧?”而保吉也只回答了一声:“是的。”但或许是因为会计官公务太多的缘故吧,迟迟没有把月饷交给保吉。不仅如此,最后身着军服的他竟然背对着保吉,一直不停地拨弄着算盘。
“会计官……”
保吉在等了一阵之后,几乎是在哀求似的叫了一声。会计官这才隔着肩膀看了看保吉。从他的嘴里显然就要迸出这样的字眼了:“很快就好啦。”然而,保吉抢在他头里,一字不差地说出了预先准备好的一句话:
“会计官,是不是让我叫一声‘汪’?对吗,会计官?”
保吉相信,他说这话时的声音肯定比天使还要柔和。
洋人
这所学校里有两名洋人,他们是来教授会话课和英语作文课的。一个是叫汤森特的英国人,而另一个则是名叫斯塔雷特的美国人。
汤森特先生乃是一个脑袋已经谢顶,而又说得一口流利口语的好心老头子。本来,若论洋人老师,不管他是何等庸俗之辈,一旦说起莎士比亚和歌德来,无一全都会口若悬河,喋喋不休。但幸运的是,汤森特先生甚至对文艺的子丑寅卯也绝口不提。有时话题中涉及华兹华斯[4]的时候,他如此这般地说道:“所谓诗歌这玩意儿,我可是一窍不通。就说华兹华斯等人吧,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
保吉曾经和这个汤森特先生在同一个避暑胜地住过,所以,在去学校和从学校回来的路上,都乘坐的是同一辆列车。火车大约要行驶三十分钟。于是,两个人就在车厢里,一边叼着格拉斯哥出产的烟斗,一边交替着谈起香烟的话题、学校的话题,还有幽灵的话题。因为汤森特先生作为一个通神论者,就算对哈姆雷特不感兴趣,至少也对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兴趣盎然吧。不过,一旦提到魔法和炼金术以及 occult sciences(神秘学)的话题,先生他必定会露出一副不胜悲戚的表情,同时摇晃着脑袋和烟斗,说道:“神秘的门扉远不像凡夫俗子们想象的那样难以开启。毋宁说其可怕之处,恰恰就在于很难轻易关闭这一点。对那种东西最好是敬而远之。”
而另一个斯塔雷特先生则是一位年轻许多而又喜好刀尺的人。冬天,他总是在暗绿色的大衣上佩带一条红色的围巾。与汤森特先生相比,他倒是喜欢不时地浏览一些新近出版的书籍。而且还在学校的英语大会上作过题名《新近的美国小说家》的大型演讲。他竟然在演讲中说,美国新近最伟大的小说家要么是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5],要么是欧·亨利[6]!
斯塔雷特先生所居住的地方,尽管不是同一个避暑胜地,但却也是沿线的某个城镇,所以,也就自然经常同坐一列火车了,至于和他谈论过一些什么话题,在保吉的记忆里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唯一记得的,是那次在候车室的暖炉前等待火车时的情形。当时,保吉打着哈欠,说起了教师这门职业的枯燥乏味。不料戴着无边眼镜、长得仪表堂堂的斯塔雷特先生一边露出微微有些奇妙的表情,边说道:
“教师可不是什么职业,我想,毋宁说应该称之为天职吧。You know,Socrates and Plato are two great teachers……Etc.(您知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可是两位伟大的教师呀 ……云云)”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是不是美国佬,这并无什么大碍。倒是他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称之为教师——这一点促使保吉打定主意,从此要对这个斯塔雷特先生抱以殷殷友情。
午休
——某种空想
保吉走出了二楼的食堂。担任文科课程的教官们在吃过午饭之后,大都喜欢步入隔壁的吸烟室里。而保吉今天却一反惯例,决定顺着楼梯下到庭院里去。这时,只见一个下士如同蝗虫一般,三步并作一步地从楼梯上跑了上来。一看见保吉,他就突如其来地行了个毕恭毕敬的举手礼,并且飞快地越过了保吉的头顶。保吉一边情不自禁地朝着阒无入迹的空间还以点头之礼,一边慢悠悠地继续拾梯而下。
在庭院里,只见罗汉松与榧子树中间盛开着好多木兰花。不知为什么,木兰树就是不肯把难得的花儿朝向光线明媚的南边。而辛夷树尽管与它非常相似,但却必定会把花儿朝向南面。保吉一边点燃香烟,一边为木兰的个性献上自己的祝福。
正在这时,就恍如从天投落的石块一般,一只鶺鸰翩然飞了下来。鶺鸰对他毫不认生,一个劲儿地摇晃着尾巴,作为给他带路的信号。
“往这边!往这边!才不是那边呐!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他就那样按照鶺鸰的指点,在铺着石砾的小径上漫步前行。但谁又知道鶺鸰是如何作想的,只见它又忽然转身飞上了天空。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个子轮机兵的出现。只见他兀自沿着小径朝这边走了过来。保吉有一种感觉,似乎曾在哪儿见过这个轮机兵。轮机兵在敬过礼之后,从他身边匆匆地走了过去。保吉一边吧嗒着香烟,一边继续思忖着那个人究竟是谁。两步、三步、五步——当走到第十步的时候,他终于恍然大悟道:那个人就是保尔·高庚。抑或是高庚的转世。他手上握着的铁铲无疑马上会变成一支画笔。而且最终还会被疯狂的朋友用手枪从背后射中。尽管令人同情,但也实属无可奈何。
保吉终于沿着小径来到了大门口前面的广场。那儿有两门作为战利品的大炮并排在松树和细竹从中。倘若把耳朵贴近炮身,会听到某种气息从中流淌而过的声音。或许大炮也是会打哈欠的吧。他在大炮下席地而坐,然后点燃了第二只香烟。这时,只见前庭中心的沙砾上,有一只蜥蜴正熠熠闪光。人一旦被砍掉了腿脚,是不可能使其再生的。但蜥蜴却不同,即便被切掉了尾巴,又可以马上重新长出一条尾巴。保吉就那样一边叼着香烟,一边想道:与拉马克[7]相比,蜥蜴无疑更是一个进化论者。可就在他观察了一阵子以后,那只蜥蜴竟不知不觉地化作了垂落在沙砾上的一抹重油。
保吉终于欠起身来。他沿着刷过油漆的校舍再次穿过庭院,来到了面向大海的运动场。在铺着红土的网球场上,几个武官教师正热衷于比赛的胜负。突然,有什么东西在网球场上的空间中发生了爆裂,与此同时,在球网的左右两侧进射出了一道浅白色的直线。原来,那不是球在飞舞,而是有人打开了香槟酒的瓶盖。并且,身着衬衫的诸神正津津有味地品赏着香槟酒。保吉一面赞美着诸神,一面绕到了校舍的后庭。
后庭里有很多蔷薇树,但还见不着一束绽开的花儿。他信步溜达着,从延伸到路上的蔷薇树枝上发现了一只毛虫。很快又看见邻近的树叶上匍匐着另一只毛虫。毛虫们相互颔首示意,就像是在议论着他或者别的什么一样。保吉决定站在那儿,悄悄聆听它们的对话。
第一只毛虫 这个教官几时才会变成一只蝴蝶呢?从俺们曾曾曾祖父那一代起,他就在这地面上四处爬行了。
第二只毛虫 没准人是不会变成蝴蝶的吧?
第一只毛虫 不,变肯定是会变的。瞧,那儿不是也有人正在飞吗?
第二只毛虫 没错,那儿是有人在飞呐。可是,别提有多么丑陋了!看来,人甚至不具备美的意识。
保吉把手搭在额前,抬头眺望着驾临头顶上的飞机。
一个恶魔摇身变成同僚,兴高采烈地走了过来。过去传授炼金术的恶魔如今竟然也在向学生们教授着应用化学。他一边嗤笑着,一边朝保吉搭讪道:
“喂,今天晚上愿不愿意陪我玩玩?”
保吉从恶魔的微笑中清晰地看见了浮士德的两行字迹:“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绿。”
在告别恶魔以后,他又转而走向校舍里面。所有的教室都空荡荡的。他在路过时朝里张望,惟有一间教室的黑板上还留着一幅没有画完的几何图。发现他在偷窥,那幅几何图认定自已会被他擦掉,于是,马上一伸一缩着,说道:“还要留着下节课时用呐。”
保吉顺着刚才走下的楼梯拾级而上,走进了外语课和数学课的教官室。在教官室里,除了秃顶的汤森特先生之外,不见一个人影。而且,为了消除无聊,这位老教师正一边吹着口哨,边尝试着跳独脚舞。保吉露出了一丝苦笑,走到化妆台前面洗手。这时,他无意中看了看镜子,令人吃惊的是,汤森特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摇身变成了一个美少年,而保吉自己则变成了一个佝腰驼背的白头老人。
耻辱
保吉在去教室上课之前,必定会预习教科书上的内容:这倒并非仅仅出自如下的义务感,认为既然自己领取了月饷,就不应该在课堂上信口开河。由学校本身的性质所决定,教科书上经常出现大量的海上用语。如果不事先好好备课,就很容易谬误连篇。比如说,有Cal’s paw这种说法,乍一看还以为是指猫的脚,结果却是徐徐微风的意思。
有一次,他给二年级的学生讲授了一篇描写航空内容的小品文。那是一篇拙劣得可怕的糟糕文章。就连狂风在桅杆上咆哮,浪涛涌进甲板上的舱口,都没能在文字中体现出来。尽管吩咐学生进行译读,可他自己却率先感到无聊起来。这种时候最容易受到一种冲动的驱使,希望以学生为对象,就思想问题和时事问题侃侃而谈。教师这种职业的人,原本就是喜欢教授学科以外的东西。道德、兴趣、人生观——无论取名叫什么都无所谓。总之,较之教科书和黑板上的内容,他更愿意教授某种贴近自己心脏的东西。但不凑巧的是,学生偏偏对学科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意学习。不,不是无意学习,而是绝对地讨厌学习。正因为保吉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百无聊赖的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行译读。
不过,不仅要倾听学生的译读,还要严格地矫正其错误,即便在不感到无聊的时候,这么做对于保吉来说,也是一件烦心的事情。在一小时的课程终于熬过了三十分钟以后,他让学生们停止了译读。接下来,由他自己开始逐节进行朗读和翻译。在教科书上航海,也同样枯燥至极。与此同时,他的授课方式也枯燥乏味得毫不逊色。他就像横渡无风带的帆船一样,忽而看漏动词的时态,忽而弄错关系代名词,举步维艰地向前行驶着。
英勇的门卫
究竟是在秋末,还是在冬初,有关的记忆业已模糊了。反正是在需要套上大衣才能去学校的时节。当大家在午餐桌上坐好之后,一个武官教师向邻座上的保吉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怪事:也就是在两三天前的深夜,有两三个强盗把小船划到学校的背后。正值夜勤的门卫试图单身擒获这帮强盗。谁知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反倒被对方抛进了大海。门卫变成了一只落汤鸡,但最后总算是爬上了岸边。不用说,强盗们的小船此时已经消失在了大海的夜幕中。
“就是那个叫做大浦的门卫。说来也真够倒霉的。”
武官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面包,一边露出了苦涩的微笑。
大浦这个人,保吉也是认识的。几个门卫常常交替着守卫在门口的值班室里。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只要看见是教官从门口进出,他们就必定会行举手之礼。保吉既不喜欢被人敬礼,也不喜欢向别人还礼,所以,当他从值班室前面路过时,总是故意加快脚步,不给门卫敬礼的机会。但惟有这个叫做大浦的门卫决不肯轻易罢休。首先,他就那样坐在值班室里,一直凝神注视着大门内外十来米远的距离。因此,只要一看见保吉的身影,不等走近,便早已做好了敬礼的架势。既然如此,也就只能当作是宿命来加以接受得了。对此,保吉总算是死心了。不,不光是死心了。相反,近来只要一瞥见大浦,就像遭到响尾蛇觊觎的兔子一般,索性率先摘下自己的帽子。
可从话中得知,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强盗抛进了大海。尽管保吉多少有些同情他,但还是忍不住笑了。
过了五六天之后,保吉偶然在车站的候车室里发现了大浦。一看见他的出现,大浦便顾不得此刻身在何地,竟然一下子端正姿势,恭恭敬敬地举起手来,朝保吉行了个礼。保吉顿时陷入了一种错觉,仿佛从他的身后清晰地看见了值班室的门口。
“你不久前……”在沉默了一阵之后,保吉这样搭话道。
“唔,结果没有能够抓住强盗……”
“受了很大的苦吧。”
“幸好身体没有受伤……”大浦一面苦笑着,一面像是自我解嘲似的继续说道,“如果真的想非抓住强盗不可,或许也不是不能逮住个把的。可是,即便就算是逮住了,不也就那个样儿吗?……”
“所谓不也就那个样儿吗,这是指……”
“也不可能得到奖赏什么的。因为在门卫守则里,对这种场合该如何处理,并没有明文规定……”
“即便以身殉职也一样吗?”
“是的,即便以身殉职。”
保吉看了一眼大浦。据大浦自己说,其实他那么做,并非就是像勇士那样以命相赌的。而是在心里掂量了一番奖赏之后,将本来应该抓住的强盗放走了的。但是,——保吉一边取出香烟,一边尽可能装得快活地朝对方点了点头。
“的确,如果是那样的话,也真是太荒唐了,结果只能是越冒险越吃亏。”
大浦说了声“啊”或者别的什么。不过,他脸上的表情却显得出奇地抑郁。
“可是,一旦给予奖赏,那么……”保吉有些忧郁地说道,“可是,一旦给予奖赏,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真的会临危不惧呢?——想来,这也多少有些值得可疑呐。”
这一次是大浦陷入了沉默之中。然而,保吉刚一把香烟叼在嘴上,他就连忙擦燃自己的火柴,递到了保吉面前。保吉一边把摇曳着的红色火苗挪向烟头,一边使劲遏止住浮上嘴角的微笑,以免被对方觉察。
“谢谢。”
“不,哪里哪里。”
在不经意说着的同时,大浦把火柴盒揣回了口袋里。但保吉坚信,自己今天又看穿了这个英勇门卫的一个秘密。那火柴上的火苗决不仅仅是为了保吉才擦燃的。事实上,是为了那些在冥冥之中审视着大浦之武士道的诸神而点燃的吧。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3年4月) 译者:唐先容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 (1885—1980)是日本和歌诗人土歧善磨的别号。 ↩
- 参见《旧约》(创世纪)第25章。烤肉疑是红豆汤之讹。以撒和利百加有孪生子以扫和雅各,哥哥以扫喜好打猎,深得父亲宠爱,而弟弟雅各则生性安静,深受母亲喜欢。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时已经累昏了,于是,哥哥向弟弟要红豆汤喝,可弟弟却要哥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自己,以扫说,我即将死去,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何意义,遂起誓卖之,于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哥哥,而以扫喝完后随即起身而去。 ↩
- Rembrandt(1606—1669),荷兰画家。他的画作多描写城市贫民、流浪者和农民的形象。 ↩
- W.Wardswarth(1770—1850),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
- 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英国小说家,而不是美国小说家。著有《宝岛》等冒险题材小说。 ↩
- O.Henry(1862—1910),美国短篇小说家。 ↩
- Lamarek(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进化论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