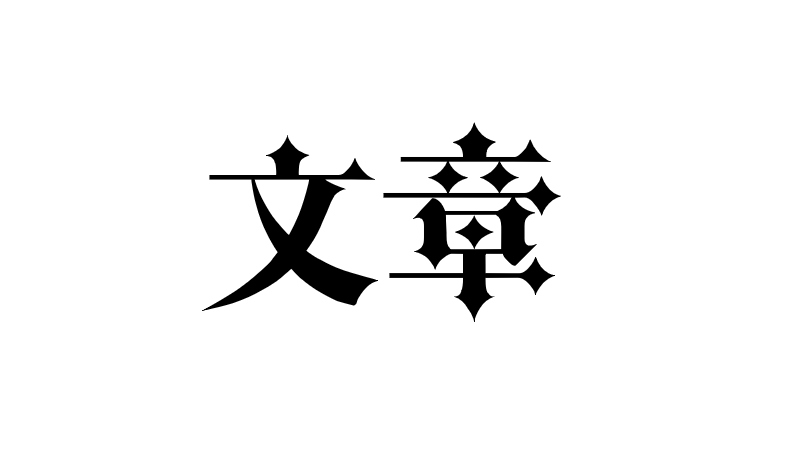
文章
文章
“堀川哪,能不能帮着写一篇悼词?星期五给本多少佐开追悼会——到时候校长要拿去念……”
走出食堂的时候藤田大佐对保吉这么说了一句,堀川保吉在这个学校教英语译读。不过在教书之余,他时常还要帮人写个悼词、编编教科书、替学生写写天皇驾到时的发言稿、翻译外国报纸的新闻什么的,一般总是藤田大佐吩咐他做这种事。大佐大概要四十岁了,他皮肤微黑,脸上的肉已经松弛,显得有些神经质。保吉跟在大佐身后走过走廊,听了大佐的话不觉地“哎呀”了一声:
“本多少佐去世了?”
大佐好像也挺意外的样子回头看了看保吉。保吉昨天偷懒没上班,结果没看见本多少佐猝死的讣告。
“昨天早上去世的。听说是脑溢血——这么着吧,请在星期六前写好,正好就是后天一早就要。”
“好吧,写倒是能写……”
藤田大佐的脑子转得挺快,没等保吉开口就说:
“我呆会儿就把本多少佐的履历表让人送过来,就当写悼辞的参考材料吧。”
“可本多少佐是个什么样的人哪?我只是见过本多少佐……”
“这个嘛,他是个重兄弟感情的人。还有——还有嘛,在班上总是学习成绩拔尖。另外嘛,你就发挥你笔杆子的本事吧。”
这时两个人已经走到黄色的科长室门前停住了脚步。藤田大佐被叫做科长,干的是副校长的差事。说到这份儿上,保吉只好把写悼辞应遵循的艺术良心抛在一边了。
“那就只有写他资性颖悟,兄弟情笃什么的,想办法凑合着写喽。”
“那就拜托了。”
和大佐分手后,保吉没去吸烟室而是回了一个人都没有的教官室。十一月的阳光正好照在窗边保吉的桌上。他在桌前坐下,给一支劣等雪茄点上火。在这以前保吉已经写过两篇悼辞了。第一篇悼辞是为患盲肠炎的重野少尉写的。当时他刚来学校,不知道重野少尉是个什么样的人,连他长得是什么样都没记住。不过,那对于他来说是写悼辞的处女作,所以多少还有点儿兴趣,所以起草了一篇模仿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写了什么“悠悠哉白云”之类的句子。第二次是为意外被淹死的木村大尉写的悼辞,他和木村大尉每天都会从避暑地到学校的车上见面,所以能很自然地表达哀悼的意思。可是这次对本多少佐,充其量到食堂的时候能看到他那像秃鹰的脸。再说了,保吉现在对写什么悼辞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要说起来的话,现在的堀川保吉成了专写悼辞的殡仪馆了,奉命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把龙灯和花圈送上门的精神生活上的殡仪馆。保吉嘴里叼着廉价雪茄,心里越来越不高兴。
“堀川教官。”
听到有人喊,保吉像从梦里醒来了似的,抬头看着站在办公桌旁的田中中尉。田中中尉嘴边留着短短的胡子,长着双下巴,很招人喜欢。
“这是本多少佐的履历表,科长让我交给您。”
田中中尉把几张纸放在了桌上。保吉只是答应了一声:“噢”,懒懒地看了看那几张纸。纸上用楷书密密麻麻地罗列着叙任的年月日。这不只是一份履历表,无论文官武官,天下所有官吏都由这样的履历表象征着自己的一生。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请教请教。不是海上用语,是小说里的一个词。”
在中尉掏出来的纸片上有几行外文,其中一个词下画着蓝铅笔印。Masochism——保吉不由得把眼睛转到中尉泛红的娃娃脸上。
“是这个词吗?这是嗜虐狂的意思。”
“好像一般的《英日词典》里没有这个词。”
保吉向中尉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脸还是毫无表情。
“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田中中尉脸上仍然露着开朗的微笑,看着这样憨厚的微笑还真让人着急不起来。现在保吉看着田中中尉幸福的样子,感动得甚至想把精神病学词典里的所有单词都塞进中尉的脑袋。
“这个词的语源——嗯——叫马佐夫吧?他的小说好看吗?”
“什么呀,全是胡说八道。”
“不过,马佐夫这个人的人格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你说马佐夫啊?马佐夫那个家伙是个笨蛋。据说他积极主张什么政府应该优先出钱支持私娼,而不是增加国防开支。”
田中知道了马佐夫的毛病后,终于把保吉解放了。其实马佐夫是不是主张政府应该重视保护私娼而不是增加国防开支,保吉也不怎么清楚,没准儿他对国防开支还是很尊重的。但是如果自己不这么说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往田中中尉这个乐天派的脑子里灌输变态性欲的可笑来历……
田中中尉走了以后,保吉又点上了一支雪茄,一边抽一边在屋里踱步。刚才已经讲过了,保吉在这里教英语。但是,这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实际上他在当老师以后,仍然会两个月左右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其中之一——把圣·克利斯托夫的传说改写成旧译《伊索寓言》风格的小说。一家杂志这个月发表了小说的一半,现在还要为同一家杂志写下个月的另一半。到了这个月的七号就必须交稿子了,现在哪是写悼辞的时候啊。每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就是不分早晚地用功,小说写得完写不完还说不准呢。保吉想到这儿对悼辞更觉得厌烦了。
当柱子上的大钟指针指到十二点半的时候,此时也就相当于牛顿的脚下掉下个苹果的时刻。现在离保吉上课还有三十分钟。要是在这段时间里把悼辞写完的话,在辛苦的工作之间就不用再斟酌“悲伤之至”之类的词儿了。当然,在仅仅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就要把追悼“资性颖悟,兄弟情笃”的本多少佐的悼辞写好,多少还是有些困难。但是如果有点儿这样的困难就害怕了的话,那么自称比上自柿本人麻吕、下至武者小路实笃还丰富的词汇量不是成了吹牛了?保吉立刻坐到桌前,蘸水笔往墨水瓶里沾了一下,开始在试卷纸上一口气地写下去。本多少佐的丧事那天是个货真价实的秋日高照的好天。保吉穿着大礼服,戴着高礼帽,跟着十二三个文职教官走在送葬行列的后面。走着走着保吉忽然回头一看,以校长佐佐木中将为首,武官有藤田大佐、文官有栗野教官,他们都比自己更靠后。保吉一下子觉得自己的位置很不合适,连忙跟走在身后的
藤田大佐打招呼:“前面请,前面请。”可是大佐只是说了声“不了”怪怪地微笑着。接着正和校长聊天的小胡子栗野教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醒着保吉:
“堀川,按海军的礼仪呀,越是大官儿就越走在后头,你可不能拉在藤田大佐的后头啊。”
保吉这下子更不好意思了。还真是的,听他这么一说,保吉才发现那个笑眯眯的田中中尉的确走在队伍的前边儿。保吉连忙大步赶到田中中尉的身旁。田中中尉今天不像是参加葬礼,倒像是来参加婚礼的,他兴高采烈地和保吉说上了:
“今天天气不错呀。——您刚来吗?”
“不是,我一直在队伍后边的。”
保吉把刚才的经过告诉了田中。中尉听了笑了起来,这笑声甚至让人觉得简直伤害了葬礼的严肃性。
“您是第一回来参加葬礼吗?”
“哪里,中野少尉的时候,木村大尉的时候都来了。”
“那时候您是走在那儿的呢?”
“当然跟在离校长和科长老远的后头了。”
“这也——您这成了大将级别了。”
这时送葬队伍已经走进离寺院不远的街上了。保吉和中尉聊着,眼睛还没忘记瞟出来看热闹的人群。这个街上的人从小就看过无数的葬礼,所以有准确估计丧葬费用的非凡才能。实际上,暑假前一天给教数学的桐山教官的父亲送葬的时候,一个身穿汗衣的老人就在站在房檐下,用扇子遮着太阳说:“哈,这丧事得用十五块钱吧。”今天也——今天不巧没有人出来露一手。不过,神道教的神官把好像是自己孩子的白化病扛在肩膀上,想起来也算是奇观了。保吉忽然想到,什么时候应该把这个街上的事写一篇名叫《丧事》或什么的短篇。
“这个月好像您写了一篇关于基督教的小说吧?”
兴致相当不错的田中大尉不停地活动着自己的舌头:
“报纸上已经有评论喽。今天的《时事新闻》、不,是《读卖新闻》。呆会儿我拿给您看,我把报塞到外套口袋里了。”
“不不,这就不用了。”
“您都有人评论了,可我却还只是想写一点评论而已。比如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性格——”
保吉忽然悟出道理来了:世上之所以充满了评论家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送葬队伍终于进了庙门。这座寺庙背靠松树林,俯瞰平静的大海,平时大概相当安静。但是今天庙门里被先于送葬队伍而来的学生们占满了。保吉在僧房外脱下新的漆皮鞋,走过西哂的长廊,来到佛堂参加丧礼人员的席位,佛堂里只有草席是新的。
弔客的对面是亲属席,在上座就坐的大概是本多少佐的父亲。他的脸长得也像秃鹰,头发全白了,可是身躯却和他儿子一样壮健。在他下手坐着的像个大学生,肯定是本多少佐的弟弟了。第三位是个姑娘,要是本多少佐的妹妹的话显得风度又太好了一点。第四位是——不过四位以下已经没什么特别突出的了。在参加葬礼的席位中首先是校长,校长的下手是科长,保吉正好在科长的身后。弔客坐成两排,但是没像校长、科长那样坐得规规矩矩,而足盘腿大坐,省得跪得两腿发麻。
和尚立刻开始念经,就像爱好艳情小调一样,保吉也喜欢听念经,不管哪一宗派念经都喜欢听。可惜的是东京、包括东京附近的寺庙就连念经也有了堕落的苗头。听说古时从金峰山的藏王庙到熊野、住吉的菩萨都到法轮寺的院子里来听高僧颂经。可是过去的妙音已经在美国文明传入的同时永久地远离现世秽土了。现在那四个徒弟就不用说了,连戴着近视眼镜的住持念佛经的高品也像小学生背诵国定教科书一样。
念经告一段落,校长佐佐木中将缓慢地走到少佐的棺木前,少佐的棺材上盖着白色的缎子,安放在佛像基座正前方的佛堂门口。在棺材前的小桌上,少佐获得的勋章和人造莲花、摇曳着火苗的蜡烛摆放在一起。校长先对着棺材施了一礼,展开左手拿着的好似贵重文书的悼词。悼辞当然是保吉两三天前写的“名文”。“名文”并没有有什么让保吉感到羞愧之处。不好意思的神经就像旧磨刀石一样,早就磨薄了。不过有一点,在这场追悼喜剧里,自己也担当了悼辞作者的角色。问题还不在这儿,自己不得不被卷到这种事里本身反正让保吉感到不大高兴。保吉在校长故意干咳几声的同时,不自觉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
校长开始用低沉的声音朗读悼辞,声音略显干涩,但是充满了超出文章和语言的沉痛,根本听不出来是在朗读别人代笔的悼辞。保吉不由得佩服起校长的演艺本领来了。佛堂里当然鸦雀无声,人们甚至连身子都不动一下。读到“资性颖悟,兄弟情笃”的时候,校长的声音更加沉痛了。突然,从亲属席里传出了吃吃的笑声。这还不算,那笑声好像还越来越大了。保吉心里紧了一下,隔着藤田大佐的肩想在对面亲属席找到那个发笑的人。这时他才发现,他以为那个不分场合发笑的声音其实是哭声。
哭声是少佐的妹妹发出的。她梳着旧式的头发,用绸手绢掩着嘴,显得风度很好。不光她,他弟弟——就是那个也很魁梧的大学生也是泪水涟涟,连老人也难过地不停用纸巾擦着鼻子。保吉面对这样的场面,首先感到特别惊讶。接着他有一种让观众感动得直哭的悲剧作者的满足感。但是他最后感觉到一种比亲属的感情更沉重、更难表达的内疚感。这是不知不觉把泥腿踩进别人有尊严的心灵、难以解脱的负疚感。保吉面对负疚感,在历时一小时的丧礼中第一次诚惶诚恐地低下了头,本多少佐的亲属们不会知道这个英语教师等人的存在。但是,保吉在心里想象着穿着丑角衣服的拉斯科尔尼科夫[1]一个人时隔七八年以后,仍然跪在泥泞的道路上执着地恳求得到大家宽恕……
丧礼那天的傍晚,保吉下了火车,穿过避暑地竹篱间的小路,朝海边租住的家走去。走在狭窄的路上,保吉鞋底上沾满了 沙子。不知什么时候雾气好像也降下来了。篱笆里有很多松树,透过松枝隐隐约约能看到天空,并且可以微微闻到松脂的清香。保吉低着头,没理会这静谧的环境,缓缓地朝海边溜达过去。
从寺庙回来的途中,他和藤田大佐走在一起。大佐对保吉写的悼辞赞扬了一番,并评论说“忽焉玉碎”一句对本多少佐实在是太贴切了。就这么几句好话,已经把看见了死者亲属眼泪的保吉捧得晕晕乎乎的了。上了火车,保吉又和老是和和气气的田中中尉碰在了一起,田中中尉把登了评论保吉小说的《读卖新闻》拿给保吉看。写评论的人是在文坛上颇有盛名的N先生。N先生把保吉的文章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对保吉宣判了死刑:文坛根本不需要海军某某学校教官的雕虫小技!
不用半个小时就写好了的悼辞出乎意料地让人感动。但是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认真推敲的小说却没有得到自己期待得到的感动之什一。当然,保吉对N先生的评论完全可以一笑付之。可是他对自己目前所处的地位却无法不当回事。他写悼辞获得了成功,写小说却失败得一塌糊涂。从他的角度想想,肯定会失去信心的。到底命运到什么时候才会为了他把这场令人伤心的喜剧的幕布拉下呢?
保吉忽然抬头看着天空。从交错的松枝缝隙中看上去,能清楚地看到天边挂着暗淡的红铜色月亮。他注视着月亮,不禁有了尿意。路上幸好一个行人也没有,路两边还是竹篱。他在右边的竹篱下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伤心尿。
小便还没完的时候,保吉眼前的竹篱忽然“吱”的一声向后挪开了。原来保吉以为眼前是竹篱笆墙,其实是别人家的木头门。一看从木头门里出来的人是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这时候保吉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慢慢把头偏向一边,硬着头皮把这泡尿撒完。
“真够呛啊。”
那个男人含含混混地嘟囔了一句,听那声音就像他自己给别人找了麻烦似的。保吉听到这声音,才突然发现天已经黑得看不见自己在撤尿了。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4年3月) 译者:宋再新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