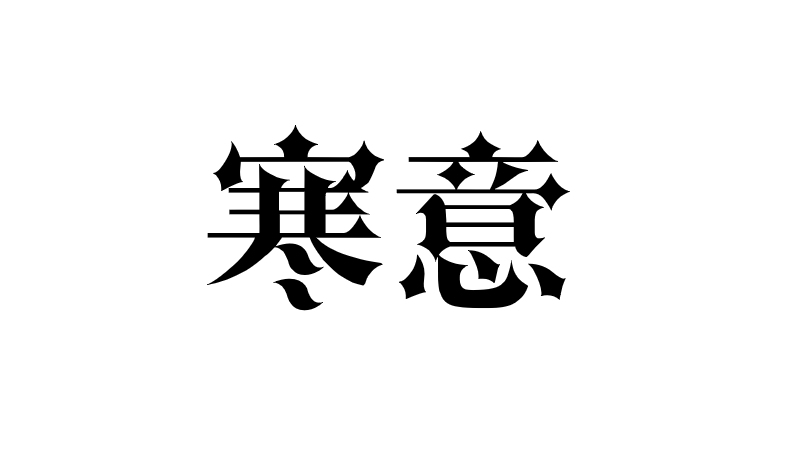
寒意
寒意
雪后的一个上午,保吉坐在物理教官室的椅子上望着火炉里的火苗。黄色的火苗像喘气一样呼啦呼啦地往上窜,然后化作黑灰落下来,这正是火焰和屋里的寒气相斗的证据。保吉忽然想起地球外宇宙的寒冷,不禁对烧得通红的煤炭产生了近乎怜悯之情。
“堀川。”
保吉抬起头看着站在炉子前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宫本的脸。戴着近视眼镜的宫本手插在裤子兜里,长着小胡子的嘴上露出老好人的微笑。
“堀川,你知不知道女人也是一种物体?”
“我知道也是一种动物,可是……”
“可不是动物,是物体。这可是我最近苦心研究发现的真理。”
“堀川,宫本说的话你可别当真。”
说这话的是另一个物理教官长谷川,他也是理工科毕业生。保吉回头看看,长谷川正在保吉身后的桌前看试卷,秃顶下的脸上满是怀疑的微笑。
“你这就不对了。我的发现能让你长谷川幸福得多。——堀川,你知道热传导的定律吧?”
“热传导?是电的什么热?”
“嗨,你们文学家真够呛。”
宫本趁这会儿功大把一铲煤倒进了蹿着火苗的火炉里。
“就是让两种不同温度的物体发生接触嘛,热就会从温度高的物体传向温度低的物体,这种热的移动一直到两种物体的温度相同为止。”
“这还用说吗?”
“这就是热传导的定律呀。我们暂且把女人当作物体,怎么样?女人为物体的话,你想想看,男人不用说也是物体喽。这样一来,恋爱就相当于热了。现在让男女接触的话,恋爱的传播也像热传导一样,从特热情的男人那里传到特不热情的女人那里,一直移动到直到二者的相恋相等为止。长谷川的情况就是这样嘛。”
“你看啊,他又开始了。”
长谷川好像还挺高兴,被逗得笑出了声。
“现在把通过面积S,在T时间内转移的热量当作E,于是——听得懂吗?H是温度,X是在热传导中计算的距离,K是不同物质相对应的固定热传导率。这样的话,长谷川的情况就是……”
宫本开始在小黑板上写下一些公式之类的东西,忽然他回过身来,像很失望似的把手上的粉笔头儿扔了:“嗨,跟堀川这个外行说这些,我的辛苦发现都显示不出来。……不管怎么说,反正像长谷川这样已经有了对象的人听了肯定开始来劲儿了。”
“实际上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公式的话,那有多好。”
保吉伸长了腿,懒洋洋地望着窗外的雪景。这间物理教官室在二楼的一头上,所以能很清楚地看到有体操器械的操场、操场对面的松树和后面的红砖建筑。还能看到海,从房子和房子之间望过去,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深色的海浪。
“不过,文学家可露脸了。怎么样,你最近出的书好卖吗?”
“还那样,根本卖不出去。作者和读者之间好像不起热传导作用。噢,对了,长谷川还不结婚哪?”
“啊,还有一个月。这里头麻烦事太多了,没法儿学习真要命。”
“等得都没法儿学习啦?”
“我也不是宫本,就是成了家,没有房子也够呛。实际上,上个星期天我几乎把全城走了一圈。看好有一家好像是空着的,可是你一打听原来已经被定出去了。”
“你说要像我这样吗?只要你觉得每天坐火车上学校也无所谓就行。”
“你住得也太远了一点儿。听说那边儿也有房子,我老婆也想住在那边儿。哎哟,堀川,你的鞋烤糊了。”
保吉的鞋不知什么时候挨着了炉子,空气里一股皮子烧糊的味儿,皮鞋还直冒水汽。
宫本一边擦着眼镜,一边瞪着迷迷糊糊的眼睛朝保吉笑着。
四五天以后,一个下霜的阴天,保吉为了赶火车,在靠近避暑地的街上拼命地跑着。路右边是麦地,左边是铁道的路基。在一个人影也没有的麦地里,传来阵阵轻微的声响,听那声响就像是有人在麦地里走。其实只是被翻起的土地里的霜破碎时发出的声音。
这时早上八点的上行火车拉着长长的汽笛,以不太快的速度通过了路基。保吉要坐的下行火车比这辆车要晚半个小时。他掏出表来看了看,可是表不知怎么回事才八点十五分。他觉得这个时间的差错完全怪这表。他心里当然觉得“今天绝对不会赶不上车。”路边的麦田渐渐变成了灌木丛。保吉点上了一支“朝日”牌香烟,心情比刚才好多了。
铺了煤阡石的路面稍稍升高后就是火车道口了。保吉走近道口时发现道口两边站满了人,他马上想到大概是火车压死人了。正好保吉看到旁边有个他认识的肉店小徒弟在道口栅栏边停了一辆自行车。保吉用拿着雪茄烟的手从后面拍了拍小徒弟的肩膀:
“嘿,这是怎么啦?”
“压着人了,刚才上行车压的。”
小徒弟快嘴快舌地说。他耳朵上带着兔皮做的护耳,脸上显得很有朝气。
“谁被压了?”
“看道口的。眼看一个学生要被压着了,他去救,结果反被压着了。八幡宫庙前不是有一家叫永井的书店吗?就是他家的女孩儿差点儿被压着。”
“那个孩子没被压着吧?”
“就是,你看在那儿哭的就是她。”
他说的“那儿”是指道口对面有一群人的地方。果然那儿有一个女孩儿,巡警正在向她问着什么。在旁边有个副站长模样的人时时对巡警说几句。那就是守道口的——保吉看见了在守道口小房子前盖着席子的死尸。他感到有点儿恶心,同时确实又觉得有些好奇。从远处好像可以看到席子下露出了两只鞋。
“那几个人在看着尸体呢。”
在这边的信号灯杆下有两三个铁道工人围着一小堆火。燃着黄色火焰的那堆火没有光亮也不冒烟,看起来冷飕飕的。一个工人把身子转过去烤着屁股。
保吉准备穿过道口。铁路靠近停车场,所以有好几条线路通过道口。他走过每条铁轨时都在猜想看守道口的那个人到底是在哪条线路上被压的。不过他马上就看到是哪条线路了。血还留在铁轨上,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两三分钟前发生的悲剧。保吉几乎是反射性地把眼睛转向了对面。可是,这并没有用。就在看到冷冰冰的铁轨上残留的那滩血的一刻,那光景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子里了。这还不算,他甚至还看到了铁轨上的血迹正冒着丝丝热气。
十分钟后,保吉到了停车场的月台上,但是走起路来仍然是晃晃悠悠的。在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看到的可怕情景。特别是那滩血冒起的热气似乎还在他的眼帘里。他想起了前几天聊过的热传导作用,血液里生命的热气正像宫本讲过的定律一样,正被铁轨不差一分一毫地、刻薄地传导着。不管是谁的生命,殉职的守道口工人也好,重罪犯人也好,都会像这样被刻薄地传导着。他当然知道这种想法没有什么意义,孝子必溺于水,节妇必焚于火。他很多次都试图这样自己说服自己。可是刚才看到的事实却给他留下了简单否定这种理论的沉重印象。
但是站台的人们根本不理会他的心情,每个人的脸看来都像很幸福似的。保吉对此感到十分气愤。特别是正在大声说着什么的那些海军军官们更是从肉体上感到不快。他点上第二支“朝口”牌香烟,朝站台尽头走去。在那儿能看到离铁轨两三百米远的那个岔道门。聚集在道口两边的人群好像已经散了。信号杆下铁路工人烧的火仍然摇曳着黄色的火苗。
保吉对那一堆火有了一种同情的感觉。不过,看到那个道口还是让他感到不安。他转过身背对着那边,又回到了站台的人群里。可是还没走几十步,就发现自己的红色皮手套掉了一只。刚才他给香烟点火的时候,摘下右手的手套是拿在手上的。回过头一看,那只手套掉在站台尽头地上,手掌那边朝上,就像无声地喊住他一样。
保吉在下霜的阴天里,想到了一只被丢下的红皮手套的里子。同时他在寒冷的世界里,感到有微微暖意的阳光洒下来。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4年4月) 译者:宋再新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