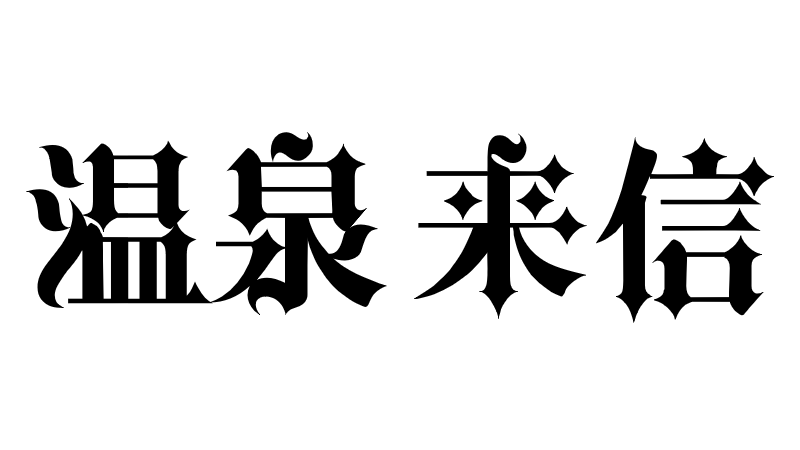
温泉来信
温泉来信
……我在这家温泉旅馆已经呆了差不多一个月了。但是,最重要的“风景”却还一张也没完成。我大体上整天就泡泡温泉、看看话本小说、在狭窄的街道上散散步,就这么一天天地打发着日子。连我自己也对自己的没出息感到失望。(作者注:在这段里,什么樱花谢了、鹡鸰来到了房顶、打气枪花了七块五、看了乡下艺人的表演、看安来小调的小戏觉得很惊奇、去山上采了蕨菜、看了消防演习、把钱包丢了等等,写了几十行。)下面就顺便按小说的形式报告一下真事吧。不过我是个外行,能不能写成小说就不知道了。只不过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有好像看小说似的感觉而已。那就请你也这么读吧。听说明治(1869年—1912年)二十年代在这里的山边住着一个叫萩野半之丞的木匠。你听了萩野半之丞这个名字肯定以为他是个多英俊的唱戏小生呢。其实他身高一米九几、体重有二百多斤,是个不比太刀山[1]逊色的大汉。不然,恐怕太刀山都要略逊他一筹。现在和我住在一家旅馆的一个姓“奈”的(在此遵从的是国木田独步的国粹式省略法),是中药批发商的少东家。他说半之丞的童心比大炮[2]还强,而他的长相简直就和稻川[3]一模一样。
无论问谁,大家都会说半之丞是个人品极好的人,而且他的技术也相当不错。不过从有关半之丞的传说都有可笑的地方来看,也许他像人家说的那样,所有的大汉智力都有点儿不够用。在进入正题前我先举个例子。据我住的这家旅馆老板说,有一回,一个刮着寒风的下午,这个温泉小镇发生大火,烧毁五十户房子。当时半之丞恰巧到离这儿一里多地的“加”字村,给人家去上梁还是十什么事。听说镇上失了火,立刻就不顾一切地往“于”字街道飞跑。经过一户农家,看见门前拴着一匹栗色的马。半之丞就想,先借来用用,等事后再跟马主人赔礼。于是一下子跨上马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上街。要是只看他这段表现还真像个男子汉。可是马一跑起来,一下子进了麦地,然后就在麦地里绕上了圈子,再一拐弯又穿过了萝卜地,猛地冲下了橘子山——等到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大汉半之丞被摔在了白薯坑里,马跑得没影了。他遭遇到了这样的灾难,当然也就赶不上救火了。这还不算,半之丞被摔得浑身是伤,连滚带爬回到镇上。等到后来才听说,原来那匹马是谁也不敢骑的瞎马。
刚巧大约在这场大火的两三年后,半之丞把自己的身体卖给了“于”字镇的“太”字医院。当然虽说是卖身体,但并不是像过去那种约好一辈子给人家干活儿。只是说约好当他死了以后,允许医院解剖自己的尸体,代价是五百块钱。不,不是现在就得五百块钱,而是死后可以得二百块钱,当前只能用契约换三百块钱。那么死后才能得的那二百块钱到底给谁呢?反正按照契约的规定,要支付给“遗族或者本人指定的人”。
实际上如果不这样写的话,那剩下的二百块钱纯粹是一纸空文。因为半之丞不用说妻子了,就连亲戚都没一个。
当时的三百块钱可是笔大数,至少对乡下的木匠半之丞来说这笔钱肯定是不少。这笔钱一到了半之丞的手,他马上就买手表、做西服、带“蓝房顶”的阿松去逛“于”字街,一下子阔了起来。所谓“蓝房顶”其实就是铁皮屋顶上涂了蓝油漆的私娼馆。听说当时还不像现在的东京样式,房檐上还吊着丝瓜呢。那里的女人好像都是乡下人,不过阿松在“蓝房顶”算是第一美人了。当然到底是什么样的美人,这我可不知道。只是据寿司店兼鳗鱼店字号叫“于”字亭的内掌柜说,阿松是个皮肤浅黑、头发卷卷的小个子女人。
我从那个老太太那儿打听到不少事。其中非常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个客人不吃橘子就写不了信,得了所谓桔子中毒症。不过这个故事等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向你报告吧。在这里我一定要把半之丞迷上的阿松杀猫的事说说。那个阿松养了一只叫“三太”的黑猫。有一天,那只“三太”在“蓝房顶”老鸨的唯一件像样衣服上撒了泡尿。不巧这位“蓝房顶”的老鸨平时最不喜欢猫,这就不是什么发牢骚不发牢骚的事了。结果听说猫的主人阿松被骂得狗血喷头,于是阿松二话没说,把“三太”揣进怀里去了“加”字河的“儿”字桥,把黑猫扔进了湛蓝湛蓝的深水里。后来——说后来可能有点儿夸张,反正我听那个老太太说的,事主老鸨当然让“蓝房顶”的人都吃了顿嘴巴,听说每个人的脸上的血痕都像蚯蚓似的。
半之丞顶多阔了一个月半个月。就算是穿西服上街,听说等皮鞋做好了连鞋钱都用光了。下边的话是真是假我也不敢保证,不过听“不”字理发店老板讲,鞋店的老板把皮鞋摆在半之承面前,低下头恳求:“大师傅,就请按成本价买回去吧。要是这双鞋谁都能穿的话,我也就不说这个话了。可是大师傅,你的鞋就像庙前门神穿的鞋。”但是,半之丞当然连成本价也拿不出来。不管问这个镇上的任何人,他们都说谁也没看见过半之丞穿皮鞋。
然而半之丞还不只是付不起鞋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好容易买的手表和西服都给卖了。那么他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呢?前前后后他一股脑全花在阿松的身上了。不过,阿松也不是光让他花钱。还是“于”字内掌柜告诉我的,说本来这里的私娼馆每年祭惠比须财神的晚上不接客,自己圈子的人凑在一起弹三弦、跳舞。但听说阿松有的时候连这时的份子钱都出不起。但是半之承还真迷上了阿松,有时阿松一发起脾气来,就抓住半之丞的胸口把他拽倒在地,然后抓起啤酒瓶子就扔过去、而半之丞不管受了什么气,仍要去讨好阿松。但是前后只有一回,半之丞听说阿松和一个别墅看门的小伙计一起去了“于”字街的时候,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大发雷霆。这话可能有几分夸张,要是照老太太的原话写的话,半之丞(作者注:虽然作为田园式的嫉妒表白不太合适,但是在这里权且割爱几行。)是这样的人。
前面已经写了,“奈”字先生所知道的大概是这个时候的半之丞。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奈”字先生和半之丞一起去钓鱼,或一起去爬“美”字岭。当然半之丞常去阿松那儿去啦、没钱用啦都是这个“奈”字先生所不知道的。“奈”字先生和正题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有意思的是,当他回到东京以后,收到了一个署名萩野半之丞寄来的包裹。包裹只有一卷毛边纸的一半大,而且特别轻。他以为是什么呢,打开一看是空的二十支装“朝日”牌香烟盒,里面塞着撒过水的青草,草上爬着几只红头萤火虫。“朝日”的空盒上还打了几个眼儿,好像是为了通空气用的。烟盒的一面用锥子乱七八糟扎满了眼儿,一看就知道是只有半之丞干得出来的杰作。
据说“奈”字先生打算第二年的夏天还要去找半之丞玩儿,但不幸的是,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因为那年秋天的秋分时节,萩野半之丞给“蓝房顶”的阿松留下一封遗书,突然莫名其妙地自杀了。那么他为什么自杀呢?要问究竟的话,比起我的报告来,还是看看他给阿松的遗书吧。当然我抄的不是遗书的原文,不过我住的那家旅馆老板的剪报册上贴有当时报纸的报道,所以大体上不会错的。
“我的嘱咐:没有钱我和你就成不了夫妇,也无法照顾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已经厌倦这个社会,所以想死。请把我的尸体送到“太”字医院(如对方来取当然更好),用这张契约交换,可以得到二百元钱。拜托拿这钱去还了我欠“安”字老板(就是我住的旅馆的老板)的帐大概够了。我实在、实在对不起“安”字老板。剩下的钱就都是你的了。一人独自离开此社会的半之丞 致阿松”
对半之丞的自杀感到意外的并不只有“奈”字先生一个人。镇上的每个人都说做梦都没想到,要是在这之前有点儿什么前兆的话,不过这也就是说说而已。不过在秋分前的一个傍晚,“不”字理发店的老板和半之丞在店前的长条凳上聊天。正在这时,“蓝房顶”的一个女人从那儿过路,那个女人一看到两个人的脸,就说刚才有个火团飞到“不”字理发店的房顶了。据说半之丞听到这话就特别认真地说:“那是刚才从我嘴里出去的。”可能那时候他就在盘算自杀的事了。但是“蓝房顶”的那个女人听了半之丞的话也就笑笑算了。“不”字理发店的老板也——不,他也笑了笑之后,心里想:“真不吉利。”
后来没过几天,半之丞就突然自杀了。而他自杀不是上吊,也不是用刀抹脖子。在“加”字河水湾里有一个用木板围起来的叫“金刚杵汤”的公共澡堂,半之丞是在那个温泉的石浴槽里泡了整整一晚上,最后引起心脏麻痹死的。还是“不”字理发店的老板说的,邻家烟店的内掌柜当晚差不多十二点的时候一个人去洗澡。这个烟店的内掌柜有妇女病,所以半夜也去洗澡。半之丞巨大的身躯那时候还泡在温泉里。咦,现在还在洗澡?这让这个平时大晌午身上缠一张手巾就敢到河里洗澡的女中豪杰也吓了一跳。而对烟店的内掌柜的问话,半之丞一声也没吭,只是在暗淡夜色中的热气里露出通红的脸来。这还不算,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直瞪瞪地看着房顶上的电灯,那样子简直太吓人了。因此内掌柜也没敢多泡,慌慌忙忙就出了澡堂子。
公共澡堂的正中央有个巨人的石头金刚杵,“金刚杵汤”由此而得名。听说半之丞在这个金刚杵前把衣裳叠得整整齐齐的,把遗书插在了衣裳旁的木屐鼻绳里。反正尸体是光着身子浮在温泉里的,要是没有遗书的话,恐怕别人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自杀的还是怎么的。我住的那家旅馆的老板说,半之丞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死法,是因为既然要把自己的尸体卖给“太”字医院,那么把解剖用的尸体弄伤了觉得对不住人家。当然这种说法在这个镇上并不是定论,嘴损的“不”字理发店老板等几个人就坚持另一种说法:“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呀,他那么干是因为弄伤了身体就得不着那二百块钱了。”
半之丞的故事就这么多了。不过昨天下午我和我住的那家旅馆老板,以及“奈”字先生一起在狭窄的街上散步,随便聊的时候又提起半之丞,现在我把那时听到的再添上。当然,对这些故事“奈”字先生比我更感兴趣,他手里提着照相机,兴致勃勃地朝戴着老花眼镜的旅馆老板打听:
“那么那个叫阿松的女人怎么样了?”
“你问阿松啊?阿松生下半之丞的儿子以后……”
“可是阿松生的孩子真是半之丞的吗?”
“确实是半之丞的,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啊。”
“那么那个叫阿松的女人……”
“阿松嫁到‘以’字酒店了。”
刚才兴致勃勃的“奈”字先生多少显得有些失望:
“半之丞的儿子呢?”
“阿松带去了。那孩子又得了伤寒……”
“死了吗?”
“没,孩子是活过来了,可是照顾孩子的阿松病了,已经死了有十年了……”
“也是伤寒吗?”
“不是伤寒,医生说是什么来着,啊,是照顾病人累的。”
正好这个时候我们走到邮局,小小的邮局是座日本式房子,嫩嫩的枫树枝伸到了邮局前。被枫树枝遮掉一半的窗子满是灰尘,隔着窗子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土布制服的年轻人正在办公。
“就是他,据说他就是半之丞的儿子。”
“奈”字先生和我都停下脚步,不自主地往窗子里看。那个年轻人一只手支着脸,一只手动着,好像是写什么。看着他的样子,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世事实在让人无可奈何。在离我们两三步远的地方站着的旅馆老板回过头,隔着眼镜看着我们,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那个家伙已经完了,整天往‘蓝房顶’跑。”
我们一直走到“几”字桥都没有人再开口说话……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5年4月) 译者:宋再新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