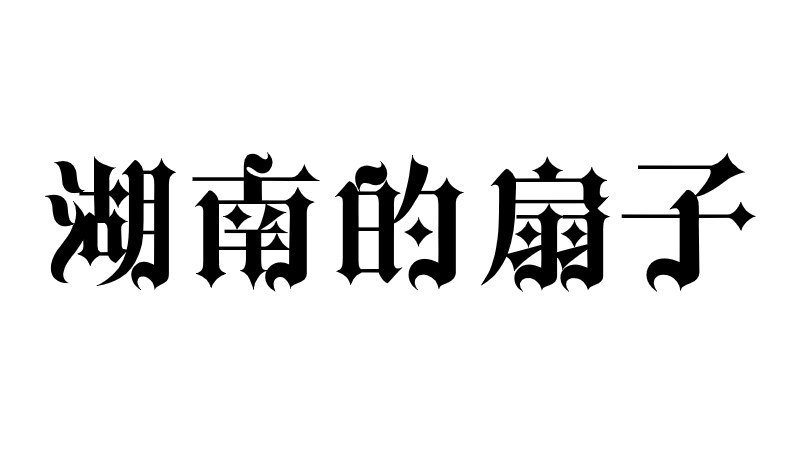
湖南的扇子
湖南的扇子
除了广东出生的孙逸仙之外,著名的中国革命家——黄兴、蔡锷、宋教仁等都出生于湖南。不必说,这一定是与曾国藩、张之洞的感化有关。但要对这种感化予以说明的话,就不得不将湖南民众所具有的那种不甘示弱的禀赋考虑在内。我去湖南旅行的时候[1],偶然遇到了一件颇具小说色彩的不入流的小事件。这一小事件,或许昭示着富于热情的湖南民众的真面目。
一
大正十年(1921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四点左右,我乘坐的沅江丸号抵达了长沙的栈桥。
在几分钟之前,我就站在甲板上倚着栏杆,眺望着从左舷方向渐渐逼近的湖南的府城。
阴云笼罩的山脚下,由白色墙垣和屋瓦搭建起来的长沙城,比想象的还要破旧。虽然在狭窄的码头一带能够见到一些新建的红砖洋房和大叶柳,但与饭田河岸[2]的景观也没有什么两样。当时,我对长江沿岸的大多数城市的梦想都已经彻底幻灭,所以事先就料想长沙恐怕也是一样,除了猪以外就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了。即便如此,眼前寒酸的景象,仍然带给了我一种近乎于失望的情绪。
仿佛十分听顺于命运的安排,沅江丸号慢慢地靠近了栈桥。与此同时,湘江蓝色的水面也缩得越来越窄。这时,一个穿着破烂的中国人,提着一个提篮一样的东西,猛地从我眼前蹿过去跳到了栈桥上。动作敏捷过人,几乎近于蝗虫一般。正惊讶间,又有一个挑着扁担的也灵巧地越过了水面。接着,两个、五个、八个……转眼之间,我眼前的视野就被无数跳上栈桥的中国人淹没了。这时,船已在不知不觉之间,稳稳地停靠在红砖洋房和大叶柳并齐排列的河岸上了。
我离开了栏杆,开始寻找同社的B君。已经在长沙呆了六年的B君,今天特意来沅江丸号迎接我,然而我却始终看不见他的踪影。并且,在舷梯前上上下下的都是一些或老或少的中国人,他们在拼命地挤来挤去,口里还大声地叫嚷着。特别是有一个老绅士在下舷梯的时候,还回过头去殴打身后的苦力。对于一路沿长江而上的我来说,这种情景都已经司空见惯。不过,这也并非是什么值得向长江表示感谢的事情,虽然它让我看惯了这一切。
我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再一次倚着栏杆,朝着人来人往的码头望去。那里,且不说我要找的B君,就连一个日本人的影子也看不到。但我却在栈桥对面枝繁叶茂的大叶柳树下,发现了一位中国美人。她穿着淡蓝色的夏装,胸前戴着一个金锁似的物件,看上去像一个孩子。在我的眼中,也许仅仅因为这一点我就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她望着高高的甲板,涂着口红的唇角露着微笑,像是在和谁打着招呼似的,将一把半开着的扇子遮在了额头上……
“嗨!”
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不知何时在我身后站了一位身穿灰色大褂的中国人,脸上堆满了和善的微笑。我一时没有认出来这个人是谁,但随即便从他的脸上,特别是从他那稀疏的眉毛上,辨认出了这位旧友。
“噢,原来是你啊!对对对,你是湖南人。”
“是的,我在这里从医开业了。”
谭永年是和我同期从一高[3]升到东大医科的留学生中的一个才子。
“你今天是来接人的?”
“嗯,你猜猜是来接谁的?”
“不会是来接我的吧?”
谭抿住嘴角,笑着做了一个鬼脸。
“我正是来接你的啊!B君不巧在五六天前得了疟疾。”
“那么,是B君拜托你来的喽?”
“不用他拜托,我原本也是打算来的。”
我想起了他从前就待人和善的往事。谭在我们的寄宿生活中,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过不好的印象。如果说在我们中间他多少有一些受人非议之处的话,正如同室的菊池宽[4]所说的,那也正是他过于不给任何人以恶感的地方……
“可是给你添麻烦,就太过意不去了。实际上,连我的住宿也都全权拜托给B君了的。”
“关于住宿已经跟日本人俱乐部说过了,住上半个月或者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一个月?别开玩笑了!能让我住上三个晚上就足够了。”
谭或许是因为惊讶,脸上的笑容立即不见了。
“仅仅住三个晚上?”
“嗯,当然,要是能看到土匪被砍头的话且另当别论……”
我这样回答道,心里猜想着这话或许会让谭永年皱起眉头来。可是,他的脸上却再次恢复了和善的笑容,一点也不介意地说:
“那样的话,你要是早来一个星期就好了。你看,那边不是有块空地吗?”
那块空地就在红砖洋房的前面,正好是在那株枝繁叶茂的大叶柳树下。但刚才树下的那个中国美人,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踪影。
“前几天在那里,有五个人一起被砍了头。看,就是那条狗走过的地方……”
“没看到真是可惜啊!”
“惟独斩首杀头在日本是看不到的。”
谭大笑之后,表情有些认真起来,但马上话题一转说:
“那我们就出发吧!车还在那边等着呢。”
二
在谭的一再邀请下,我在第三天即十八日的下午,决定去游览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麓山寺和爱晚亭。
两点左右时,我们乘坐的汽艇,在此地居住的日本人称之为“中之岛”的三角洲右侧向前行驶着。晴空万里的五月天,两岸风景格外地鲜亮秀丽。在我们右侧是连绵的长沙城,白墙和屋瓦闪耀着光芒,已经全然没有了昨天那般的阴郁。筑着长长石墙的三角洲上,生长着茂盛的柑橘林,并且随处可以窥见小巧的西式洋房。挂在洋房之间晾衣绳上的衣服也反射着阳光,显得饶有生气。
谭为了便于向年轻的船主下达命令,一直站在汽艇的船首。其实他并没有怎样下达命令,而是始终不停地和我搭话。
“那就是日本领事馆……用这个望远镜看……右边是日清汽船公司。”
我叼着雪茄烟,一只手搭在船沿的外侧,观赏着不时击打着手指的湘江水的水势。谭说话的声音是进入到我耳鼓里惟一的噪音。但是,按照他所指的方向环视着两岸的风景,也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的不快。
“这个三角洲叫做橘洲……”
“啊,有鹰在叫。”
“鹰?……噢,这里有很多鹰的。在张继尧跟谭延闿打仗的时候,当时张的几个部下的尸体顺着江水流到了这里,每个尸体上都落了两三只的鹰……”
正当谭讲着话的时候,另一艘汽艇在相隔七八米处与我们的汽艇擦身而过。那只艇上除了身穿中式服装的青年男子之 外,还坐着两三个浓妆艳抹的中国美人。其实最初我并没有留意那几个美人,而是一直在注视着那艘汽艇向前乘风破浪的雄姿。可是谭刚把话说到一半,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后,突然像发现了敌情一般急忙把望远镜递给了我。
“快看那个女人!那个坐在船头上的女人。”
我是一个越是这样被人催促越是要刨根问底的人,这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倔强的根性使然。这时,那艘汽艇驶过去溅起的浪花冲刷着我们的船板,已经弄湿了我的袖口。
“为什么?”
“嗨,先别问为什么,快点看!”
“是美人吗?”
“对对,美人!美人!”
他们乘坐的汽艇已经离开了将近二十米远,我才慢慢地扭过身子,调节着望远镜的焦距。那艘汽艇给了我一种突然向 后方退了一下的错觉。在圆圆镜头里的风景中,“那个女人”正斜着身子,好像在听别人说话,脸上不时地溢着微笑。她下颚方方的,除了一双大大的眼睛之外,并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美丽的地方,但她额前的刘海和身上淡黄色的夏装不停地随风飘动着,远远地看去却也非常漂亮。
“看见了吗?”
“嗯,连睫毛都能看得见,可是也并不怎么漂亮啊。”
我转过头来面对着一脸得意的谭问道。
“那个女人到底怎么了?”
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滔滔不绝,而是慢悠悠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反问说: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吗?在栈桥前面的那片空地上有五个土匪被杀了头。”
“嗯,我还记得。”
“那一伙人的老大叫做黄六一,他也被斩首了。据说他右手拿步枪,左手拿手枪,能同时发枪射杀两个人,在湖南是恶名远播之徒……”
谭开始讲起了黄六一一生的恶行,他所说的绝大部分内容,好像都是来自于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但所幸那些故事并不十分血腥,反而极其富于浪漫色彩。诸如黄六一生前被走私团伙称为黄老爷;从湘潭一个商人的手里抢夺过三千元大洋;曾经将腿部被枪弹击中的副头目樊阿七扛在肩头游过了芦林潭;在岳州的一个山路上曾射杀了十二个步兵等等……谭非常热心地讲述着这些故事,甚至让人觉得他对黄六一近乎于崇拜一般。
“你要知道,那家伙据说杀人掳人共犯案达一百一十七件之多!”
他不时地在故事中间加入这样的注释。当然只要土匪未给我带来任何危害,我也绝非讨厌土匪。可是,多是一些大同小异的勇武之谈,这多少让我感觉到有些乏味。
“那么,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呢?”
谭这才嘻嘻一笑,讲出了正如我所预料的答案。
“那个女人就是黄的情妇。”
我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发出惊叹,但如果只是一脸漠然地叼着雪茄烟,也未免稍嫌尴尬。
“呵,土匪也是很风流的嘛。”
“哪儿呀,像黄这样的还不算什么呢。前清末年有一个姓蔡的强盗,月收入能达一万大洋以上呢。这家伙在上海的租界外边有座豪华的洋馆,不要说太太,连小老婆就……”
“那么,那个女子是妓女吗?”
“嗯,是一个叫做玉兰的妓女,在黄生前也是相当威风的……”
谭好像想起了什么,缄口沉默着一边浅浅地露着微笑。不一会,他扔掉了香烟,认真地和我商量说:
“在岳麓有一所湘南工业学校,咱们先去参观一下怎么样?”
“嗯,看看也不妨。”
我的回答有点犹豫,那是因为昨天早晨去参观一个女校时,那里异常强烈的排日气氛曾令我不快。可是我们乘坐的汽艇却没有顾忌我的心情,绕着“中之岛”前端转了一个大弯后,便在晴碧的水面上径直朝岳麓驶去。
三
那天晚上,我和谭一起登上了一家妓馆的楼梯。
在我们走进的二楼一个房间里,中间摆放着一张桌子,还有椅子、痰盂、衣柜等,屋里的摆设与上海、汉口的妓馆几乎没什么两样。只是在房间天井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做工精细的铜丝鸟笼挂在玻璃窗的一旁。笼子里有两只松鼠全无声响地在栖木上跳上跳下。这个鸟笼跟挂在窗子和门上的红色印花布一样,都是未曾见过的稀罕之物。但至少在我的眼里,它们令人不甚舒服。
到房间里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微胖的老鸨。谭一见到她,便与她喋喋不休地谈论起来。老鸨也使出浑身解数殷勤而圆滑地应答着。可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当然是因为我不懂中国话的缘故。但据说即使能听懂北京官话,也未见得听得懂长沙的方言)。
谭与老鸨说完之后,与我在红木桌上相对而坐,然后开始在老鸨拿来的活版印刷的局票上填写妓女的名字:张湘娥、王巧云、含芳、醉玉楼、爱媛媛……这些名字对于我这个旅行者来说,无一不和中国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格外地相称。
“把玉兰也叫上吗?”
我虽然想回话,不巧老鸨正递来一根点燃的火柴为我点烟。谭隔着桌子看了一下我的脸,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了下去。
这时,阔步走进来一个戴着细细的金丝边眼镜,气色极佳,脸蛋浑圆的妓女。她穿着白色的夏装,上面镶着几颗钻石在闪闪发光。体格如同网球选手或游泳健将一般。在她的身上,我所感受到的既不是美丑也不是好恶,而是一种奇妙而痛切的矛盾。她和这间屋子里的空气——特别是和那鸟笼里的松鼠显得格格不入。
她用眼神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连蹦带跳地靠到了谭的身边。她在谭的旁边坐下之后,便将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膝盖上,开始与他声调婉转地聊了起来。谭自然也是十分得意地“是了、是了”地应答着。
“她是这里的妓女,名叫林大娇。”
被他这样一说,我马上想起了谭原本是长沙城里少有人能够攀比的富家公子。
十分钟过后,我们依然相对地坐着,开始享用有木耳、鸡肉、白菜之类的四川风味的晚餐。除了林大娇之外,又来了一群 妓女将我们团团围住。在她们身后,五六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操琴而坐。妓女们时而端坐着用仿佛是被胡琴吊得高高的音调尖声地唱起曲来。当然我并非对此全无兴趣,只是比起京调的《挡马》或者西皮调的《汾河湾》来,我对坐在我左边的一个妓女更感兴趣。
在我左边坐着的,正是我前天在沅江丸号上看到的那个中国美人。她淡蓝色的夏装上依然挂着一个金锁。可在近处一看,她虽然有着病态般的柔弱,却没有那种未经世事的纯真。我看着她的侧脸,想起了在背阴的土地上生长的小小的球茎。
“喂,在你旁边坐着的……”
谭因为喝了老酒而涨红的脸上依然笑容可掬,他隔着盛着大虾的盘子突然对我说道。
“她叫含芳。”
我看了一下谭,不知为何顿时失去了要将前天的事情告诉给他的兴致。
“这个人说话很好听,R的发音跟法国人一样。”
“嗯,她是北京出生的。”
含芳好像知道我们在谈论关于她的话题。她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瞟视着我,一边语速极快地跟谭相互问答着。但是如同哑巴一样的我,此时除了比较着二人的神色之外,便一筹莫展了。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来长沙的,我说你是前天到的,她说她前天也去码头接人了呢。”
谭对我翻译完之后,又和含芳聊了起来。她两腮含笑,像小孩子一样一个劲地摇着头。
“嗨,无论怎样她也不肯坦白。我问她是去接谁的……”
这时,林大娇突然用手中拿着的香烟指着含芳说了一句什么,好像是在嘲笑她。含芳似乎非常惊讶,一下子将两手扶在了我的膝上。好不容易渐渐恢复了笑容之后,她马上回击了一句。我不由得对这个戏剧性场景,以及这个场景背后隐藏着的她们之间相互很深的敌意,抱有极大的好奇心。
“喂,她说什么?”
“她说不是去接谁,而是去接妈妈的。而刚才这里的一个先生说她是去接一个长沙的叫×××的戏子的。”(不巧的是惟独那个演员的名字我没能记在笔记上。)
“妈妈?”
“所谓的妈妈不是亲妈,而是指养着她和玉兰等人的妓馆的老鸨。”
谭回答完我的问题,昂头喝了一杯老酒,马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什么来。除了“这个、这个”之外,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只见老鸨和妓女们都在饶有兴致地听着,好像说的是她们很感兴趣的事情。并且她们还不时地朝我瞥上一眼,由此看来,她们的话题至少有一部分是和我相关的。我一度装做若无其事地叼着烟卷,但最后也终于沉不住气了。
“混蛋!你在跟她们说些什么?”
“什么?我说今天我们在去往岳麓的路上碰见了玉兰。然后……”
谭舔了舔上唇,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
“然后告诉她们说你特别想看杀头。”
“什么呀,真没意思!”
我听了他的解释,不但对尚未露面的玉兰,就连对她的朋友含芳也没有了多少同情心。可是当我看到含芳的表情时,理智上我已经清楚了解了她的心情。她摇荡着耳环,在桌下的膝盖上反复摆弄着手帕,解开又系上,系上再解开。
“那么,你看这个也没意思吗?”
谭从身后老鸨的手里接过一个小纸包,得意洋洋地将它打开。再打开一层后,里面包着一片薄脆干点一样大小的,已经发干了的巧克力色的奇怪的东西。
“什么呀?那是。”
“这个吗?这不过是块饼干嘛……我不是跟你说过一个叫黄六一的土匪头目吗?这上面沾了黄的首级上的血。这可是在日本见不到的。”
“拿那种东西做什么用呢?”
“做什么用?当然是吃喽!这一带到现在还在相信吃了这个可以除病消灾呢。”
谭一脸清爽地微笑着,向正要离开桌子的两三个妓女寒暄应酬了几句。当他看到含芳也站起来想要离开时,便几乎乞求般地笑着说了些什么,并在最后举起了一只手,指向了坐在对面的我。含芳稍微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露出笑容,又在桌前坐了下来。我觉得她特别可爱,便避开众人的眼睛,偷偷握住了她的手。
“这样的迷信实属国耻,我作为医生从职业的角度曾不厌其烦地劝说过,可是……”
“这只是因为有杀头的关系,在日本也有吃烧焦了的人脑的呢。”
“怎么会?”
“没有什么会不会的,我就吃过。当然还是在很小的时候……”
我在说话的时候注意到玉兰走了进来,她站着和老鸨说了几句话,然后在含芳的旁边坐了下来。
谭看见玉兰来了,便又把我撂在了一边,和她亲热地攀谈起来。她比在外面从远处看时又多了几分美丽。每当笑的时候,她便会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那牙齿像珐琅一般熠熠发亮,煞是好看。但我从她整齐的牙齿不觉联想到了松鼠。松鼠这时仍然在挂着红色印花布的玻璃窗旁边的鸟笼里熟练地跳上跳下。
“来,吃一口怎么样?”
谭掰开了一块饼干,断裂处也是同样的颜色。
“净说混账话!”
我当然摇头拒绝了。谭大声笑着,又拿着饼干劝身边的林大娇吃。林大娇皱了皱眉,斜着身子把他的手挡了回去。他反复地和几个妓女开着同样的玩笑,一来二去,最后他依然是一脸微笑地,把褐色的饼干递到了不动声色的玉兰面前。
我突然有一种想要闻一闻那块饼干的冲动。
“喂,让我也看一看!”
“嗯,这边还有一半。”
谭像个左撇子一样把剩下的那一片扔给了我。我从碟子和筷子中间把那薄薄的一片捡了起来,但是好不容易捡起来之后,我却突然失去了去闻的兴致,悄悄地把它丢到了桌子底下。
这时,玉兰看着谭,与他说了两三句话,然后接过饼干,面对着盯着她的一桌人语速极快地说了一句什么。
“我给你翻译一下如何?”
谭把胳膊顶在桌子上用手托着下巴,用已经不太利索的口齿向我问道。
“嗯,你翻译一下吧。”
“听着,我逐字逐句地翻译。我非常高兴地品尝我深爱的……黄老爷的血……”
我感觉到身体在颤抖,那是扶在我膝上的含芳的手在颤抖。
“诸位也请像我一样,将你们所深爱的人……”
在谭还在说话间,玉兰已经开始用她那美丽的牙齿嚼动着那一片饼干了……
四
我按照预定计划住了三个晚上。五月十九日下午五点左右,同来的时候一样,我将身子靠在了沅江丸号甲板的栏杆上。白色墙壁和屋瓦组成的长沙城依然令我不快,这或许也是受了渐渐迫近的暮色的影响。我叼着雪茄烟,不时地想起谭永年那张亲热地微笑着的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谭永年没有来送我。
沅江丸号从长沙出发的时候,大约是在七点或者七点半。我吃过饭,在船室里昏暗的灯光下,开始计算我这几天的停留所花掉的费用。眼前不足两尺长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把扇子,粉红色的流苏垂在桌子的边缘。这把扇子,是在我来这里之前谁把它忘在这里的。我拿着铅笔计算着,又不时地想起谭永年的脸。我不太明白他那样折磨玉兰的原因,但是我停留花去的费用——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换算成日本货币的话正好是十二元五角。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6年1月) 译者:秦刚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