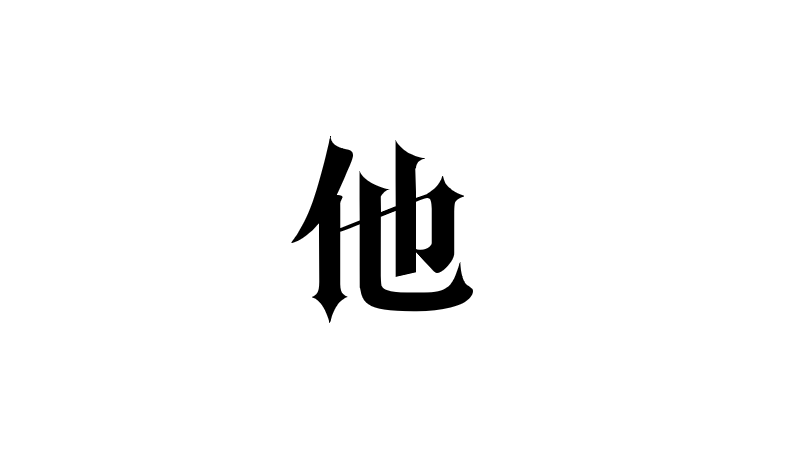
他
他
一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老朋友——他。他的名字在这儿还是不说得好。他从叔叔家出来以后,就在本乡的一家印刷厂楼上租了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住。楼下的轮转印刷机一开动,他的房间就像小蒸汽船的船舱一样,房子喀嗒喀嗒直晃悠。我还是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时,吃过宿舍的晚饭,经常到那家二楼去玩儿,这时我就能看到在玻璃窗下,他总是弯着比别人瘦一圈的脖子玩扑克算命。他的头上吊着一盏黄铜油灯,总是给他投下一圈影子……
二
他在本乡叔叔家住的时候,和我一样上得是本所第三中学。他住在叔叔家是因为他没有父母。虽说是没有父母,但是他母 亲好像并没有死。比起父亲来,他对母亲——他对已经在哪儿再婚的母亲还有少年似的感情。有一年的秋天,他曾经有点儿结巴地告诉过我:
“最近我打听到了我妹妹(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有个妹妹)嫁人的地方。这个星期天一块儿去好不好?”
我和他立刻就到离龟井户很近的场末街道去了。他妹妹嫁人的地方比预料的好找,就是理发店后面的一栋长房子中的一间。丈夫似乎到附近的工厂还是什么地方上班不在家,给婴儿吃奶的妻子——他的妹妹,正在质量和陈设都很差的屋里,此外没有其他人,虽说是妹妹,但是比他更像大人。另外除了眼角长之外,他妹妹和他一点儿都不像。
“这孩子是今年生的?”
“不,是去年。”
“结婚不也是去年吗?”
“是前年三月。”
他像遇上什么大事似的拼命地和妹妹说着话,他妹妹只是一边逗着婴儿,一边笑眯眯地答应着。我端着倒有苦涩粗茶的五郎八做的大粗茶碗,看着门外红砖墙上的苔藓,同时听着他们不太投机的谈话,感到有些感伤。
“妹夫他人怎么样?”
“怎么样?……是个喜欢看书的人呢。”
“什么书?”
“评书唱本什么的。”
实际上窗户下的确有一张旧桌子,旧桌子上有几本书——可能评书唱本也在上边吧。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可惜没记着有书,倒是在笔筒里插了两根鲜艳的孔雀毛。
“我下回再来玩儿。帮我问候妹夫。”
他妹妹仍然让婴儿含着奶头,沉静地和我们道别:
“要走啊?那记着给大家问好。对不起,就不给你们收拾木屐了。”
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我们在本所的街上走着。他肯定对第一次见到的妹妹的态度很失望。但是,我们像商量好了似的,谁也没把这样的心思说出来。他——我现在还记得,他只是用手指摸着路边的竹篱笆墙,跟我说了这样的话:
“就这么往前不停地走,手指会感到奇怪的震动感,真就像过了电一样。”
三
他中学毕业后,就决定考第一高等学校。但是,非常可惜,他落榜了。他到印刷厂的二楼租房子住就是在落榜以后的事。也从那时,他开始迷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我当然对社会科学的知识一窍不通。但是,对资本啦、剥削之类的词汇抱有一种尊敬——或者说感到恐怖。他经常利用这种恐怖驳斥我。魏尔兰、兰波、波德莱尔等是当时的我的比偶像还偶像的诗人。但是,这些人对于他来说只是麻药和鸦片的制造者而已。
我们那时的争论到现在看来,都是些不成其为争论的东西,可是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动了真格的,互相反驳着对方。只有我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叫K的医学生总是对我们冷言冷语:
“与其为了这种辩论生气,倒不如和我到洲崎[1]去。”
K看看我们两个人冷笑着对我们这么说。我内心里当然很想去,管他是洲崎也好、还是什么地方也好。但是看他那超然(实际上他那种态度也只能用超然来形容)地叼着香烟的样子,我可不想理他。不仅如此,我还要占得先机,挫掉他的锐气。
“所谓革命就是社会性的月经嘛……”
在第二年的七月,他考进了在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在以后的那半年左右大概是他最幸福的时光了。他不断的给我写信,报告他的近况。(在信里他总是罗列他读过的社会科学的书名。)可是,他不在东京让我感到生活上好像缺了点儿什么似的。我和K见面的时候肯定要聊聊关于他的消息。K也——K对他表现出来的不是友谊,而是某种兴趣,近乎科学的兴趣。
“那家伙怎么看他都长不大。可是这么一个美少年,却让人产生不了同性恋的兴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K背靠宿舍的玻璃窗,非常认真地向我打听他的事,一边还灵巧地把“敷岛”牌香烟喷出一个个烟圈。
四
他进入第六高等学校不到一年就成了病人,回到他叔叔家,病名是肾结核。我经常带着饼干什么的去他住的书生[2]房间去看他。他总是坐在床上抱着细细的膝盖,说起话来想不到还相当开朗。但是我不能不注意到搁在他房间角落里的便器,透过普通玻璃可以明显地看到血尿。
“我这样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不能忍受监狱的生活了。”
他这么说过后自己苦笑着。
“你看巴枯宁[3]的照片就知道,他的身体多强壮啊。”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他的话题,这就是对他叔叔的女儿的非常纯粹的恋爱。他从来没跟我提起他的恋爱。不过有一天下午,一个樱花期的阴天下午,他突然对我讲了他的恋爱。突然?——不,并不见得突然。我像所有的青年一样,从看到他的堂妹时起,我就对他的恋爱有一种期待感。
“小美代和学校的伙伴到小田原去了。我最近不经意看了小美代的日记……”
我对他这个“不经意”多少有点儿想加以冷笑。但是,我当然什么也没说,等着他接着往下说。
“于是我发现她写了她和在电车上认识的大学生的事。”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着要忠告小美代—下……”
我终于忍不住了,给他加了这样的评语:
“你这是自相矛盾嘛。你爱小美代就行,小美代爱别的人就不行——哪儿有这样的道理啊。要是作为你个人的心情的话那又是别的问题了……”
他明显地不高兴了。但是,他对我的话没有加任何反驳。然后——然后又说什么来着?我只记得我自己也不高兴了,这当然是因让病人的他不高兴而不高兴。
“那么,我走了。”
“那再见。”
他点了点头后,好像故意装得很轻松的样子说:
“帮我借几本书好吗?你下次来的时候带来就行。”
“什么样的书?”
“天才的传记什么的就可以。”
“那我把《约翰·克里斯朵夫》给你拿来。”
“啊,不管什么,只要有活力的就行。”
我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回到了弥生町的宿舍,不巧窗玻璃破了的自习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在昏暗的电灯下复习德语语法,但是无论如何我对失恋的他——就算他失恋了吧,反正对有叔叔的女儿的他感到羡慕不已。
五
过了大约半年后,他要转到海岸边气候好的地方去疗养。虽说是到气候好的地方,但是大体上还是每天住在医院里。我利用学校的寒假跑老远的路去看他。他的病房在不向阳又漏风的二楼,他坐在床上,仍然挺精神地笑着。但是,有关文艺和社会科学的事几乎一句也没提。
“我每次看到那棵棕榈树都有一种奇特的同情感。你看,那上边的叶子在动吧……”
在玻璃窗外棕榈树树梢的叶子被风吹动,这些叶子又摇动了全部的叶子,使叶子间微微裂开的尖端神经质似的颤抖着,这些叶子实际上带有近代式的哀愁。我思考到在这间病房里仅有他一个人,尽可能回答得明朗些:
“确实在动呢,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过是海边的棕榈树罢……”
“还有呢?”
“这就完了呀。”
“多没劲哪。”
我们这样交谈,渐渐令人。
“《约翰·克里斯朵夫》看了吗?”
“啊,看了一点儿……”
“看不下去吗?”
“这也太有活力了。”
我又拼命地想把话题从沉闷中拉回来。
“听说最近K来看过你?”
“啊,来了当天就回去了。来聊了一阵生体解剖还有其他什么的。”
“那家伙挺让人讨厌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吃过晚饭,正好风停了,我们准备到海边去散步。太阳已经沉下去了,可是周围还是很亮。我们在长着低矮松树的沙丘斜面坐下来,看着两三只海雀飞翔,聊了很多。
“这沙子多冷啊。但是你把手一直插进去试试。”
我照他说那样把一只手插进长有干枯了的燕麦的沙子里,我发现太阳照射的热量还多少残留着。
“嗯,感觉有点儿不舒服。到了晚上还热吗?”
“哪里,立刻就冷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清楚地记着这些对话。还有对面离我们有一百来米的黑沉沉的太平洋……
六
我接到他的死讯恰好是第二年的旧历正月初一。后来听说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为了庆祝旧历新年,玩歌留多牌[4],一直玩到深夜。他听着喧闹声睡不着觉就发了脾气,在床上躺着大声把他们骂了一顿。就在同时他一下子大喀血,马上就死了。我注视着带黑框的他的照片时,与其说感到悲伤,毋宁说感到了人生无常。
“又故人所持书籍已与遗骸一并烧却。倘有您所借与书籍羼入其中,还望宽宥。”
这是那张明信片一角用毛笔写得一段话。我看着这段话,想象着几本书化为火焰升腾的光景。当然那些书里我借给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册也肯定在里边,这个事实对于当时感伤的我似乎是一种象征。
又过了五六天以后,我和偶然遇到的K说起了他的事,K依旧是一副冷淡的样子,而且还叼着香烟,向我打听这样的事:
“x懂得女人了吗?”
“这个……怎么说呢……”
K像怀疑我似的盯着我的脸:
“算了,怎么都无所谓……可是x死了,你难道没有那种像胜利者的感觉吗?”
我稍稍犹豫了一会儿,这时K打断了我的话,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至少我有这样的想法。”
从那以后,我对遇到K多少感到有点儿不安。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6年11月) 译者:宋再新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