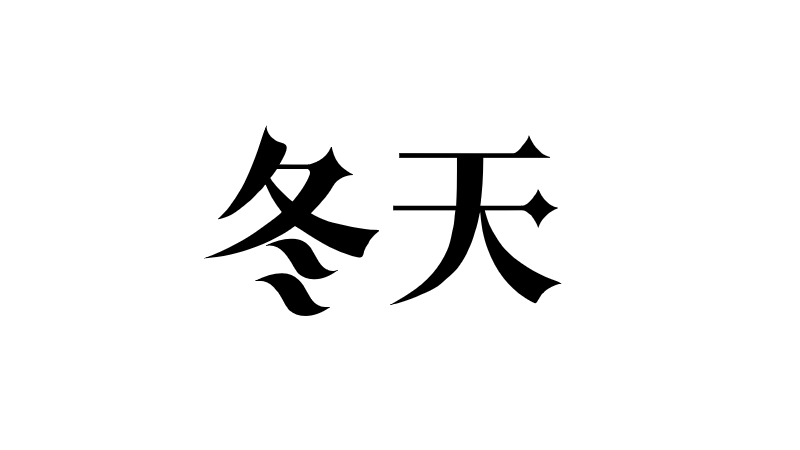
冬天
冬天
我穿着厚重的外套,戴着俄国羔皮帽,走向位于市谷的监狱。四五大前我的表姐夫进了那里的监狱。为了安慰表姐夫,我只是作为全体亲戚的代表去的,当然我内心里也的确有对监狱的好奇心。
尽管临近二月的街道上大甩卖的旗帜还没撤,但是不管是哪条街都已进入了冬季的不景气。我爬上坡路,自己也切身地感 到了疲惫。我的叔叔去年十一月因为得喉头癌去世了。过了没多久,我这个表姐夫正月里就离家出走。然后——但是表姐夫被关进监狱,对我却是个很大的打击。我必须和表姐夫一起办我最不擅长的交涉。而且和这些事交织在一起会引起和亲戚们感情上的纠葛,也常会引起一些不在东京生活的人的难以沟通的抵触情绪。我确实打算见过表姐夫后,至少到哪儿去静养一个星期……
市谷监狱外围着高高的土堤,土堤上的草已经枯黄了。而有中世纪遗风的大门上,粗木格子门扇里,可以看到霜打蔫了的桧树,铺上砂石的院子。我站在这座门前,朝一个留着半白的长胡子、看起来面善的看守递上名片,然后被带到离门不远、房檐上有厚厚的干苔藓的探视大休息室。那里除我之外,还有几个人坐在铺有一层薄布的椅子上。里面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一个披着黑色皱绸披风、正在看杂志的三四十岁的女人。
一个莫名其妙哭丧着脸的看守时时到这间屋子里来,用没有一点抑扬顿挫的声音按顺序叫着轮到探视的号。但我等了很久却怎么也不叫我的号。等了很久——我进监狱的门时刚到十点,可是现在我的手表已经是差十分下午一点了。
我的肚子当然开始饿了,可是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屋子里冷得要命,连个火星都没有。我不断地跺着脚,强压着不耐烦的脾气。可是大多数来面会的人都好像无所谓的样子。特别是一个两件和服外套重着穿、像是个搞赌博的男人也不看报,光是慢悠悠地吃着橘子。
可是随着一个个被看守叫到,一大堆来探视的人渐渐少了。我终于走到探视人休息室前,开始在铺了砂石的院子里走了起来。那儿能晒到冬天的太阳,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刮起来的风也薄薄地吹了我一脸土。我赌气,决心不到四点绝不进屋。
可是到了四点还没叫到我。不仅如此,眼看比我后来的都叫到了,人都快走光了。我最后还是进了探视人休息室,和那个像是搞赌博的人打了招呼,就打听起我是怎么回事。那个男人也不笑,用像唱大阪琴书一样的语调只回了我这么一句:
“一天只准见一个人,在你之前没准儿有谁来过了吧。”
他的这番话当然让我担心起来。我又去问那个来喊号的看守到底我能不能见到我的表姐夫,可是看守不但不回答我的问话,而且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走了。而就在这时那个像搞赌博的男人和其他几个人跟在看守身后走了。我在房子的中间机械地给烟点着火。随着时间的逝去,我心里越来越恨那个哭丧脸的看守。(自己受了这样的耻辱却突然不生气了,我总是对这点感到不可思议。)
看守又出来喊号了,这时刚到五点,我又一次摘下俄国羔皮帽,想问看守同样的问题,可是这时看守摇摇头,还没我说呢就急匆匆朝对面走了,“要说过分也太过分了”这句话正好用来形容我当时瞬间的心情。我把抽了一半的香烟扔下,走到了探视人休息室对面的监狱内门。
上了内门的石头台阶往左拐,从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穿和服的人正在办公。我打开玻璃窗,尽量用平静的口气对那个穿带家徽黑捻线绸衣的男人说话。但是我自己都能明显地意识到我那时的脸色已经变了。
“我是要见T的探视人。我能不能见到T?”
“请等叫你的号吧。”
“我从十点钟就等起了。”
“总会来叫你的吧?”
“不来叫我也得等着吗?要等到天黑吗?”
“哎呀,请再等一会儿嘛。反正只有请你等着。”
对方好像有点怕我闹起来,我在生气的同时又有点儿同情那个人。“我是亲戚的总代表,这家伙就是监狱的总代表。”——我不由得觉得很好笑。
“已经五点过了,请想个办法让我见上一面吧。”
我扔下这么一句话就先回探视人休息室了。天已经快黑了,探视人休息室里那个头上盘着发髻的女人把杂志摊在膝盖上,把头抬了起来。认真看看她的脸,觉得她什么地方像哥特式的雕刻。我在那个女人前坐下,心里还在对整个监狱感到弱者的反感。
当我终于被叫到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这回我被一个眼睛滴溜溜直转、显得很精干的看守带着,终于进了会见室。名曰会见室,其实房间最多有两三尺见方。除了我进的门外,一排还有好几扇涂漆的门,就像公共厕所。会见室的正面隔着窄廊有一扇半月形的窗子,要探视的人就从这扇窗子对面露出脸来。
表姐夫从那扇窗子的那边——缺少光亮的窗子对面伸出了圆圆胖胖的脸。没想到他的样子没什么变化,这让我放下了心。我们都不相信感伤主义,就简短地把要紧的事说了。但是在我右边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好像是看望她哥哥,一个人在没完没了地哭着。我和表姐夫说着话,还总要为右边的哭声分心:
“这回的事我全是冤枉,请你一定和大伙说说。”
表姐夫一字一板严肃地说着。我盯着表姐夫,对他的话没作回答。可是什么都不回答这本身却让我感到窒息。实际上我的左邻,一个头发有斑秃的老人也在对着半月窗和像他儿子的男人说着:
“没见到你的时候,我一个人想起了好多好多,可是一见了面就给忘了。”
我走出会见室的时候,感觉到有什么地方有点儿对不住表姐夫的。但是我也感到了作为亲属的连带责任。我又被看守带着大步穿过寒冷刺骨的监狱走廊走向内门。
住在山手地区的表姐夫家里,我的有血缘关系的表姐一个人应该等了我一天了。我穿过杂乱的街道,好容易才走到四谷见附车站,坐上了满员的电车。说“没见到你的时候我一个人”的那个有气无力的老人的话现在还留在我的耳边。我觉得这句话比那个女孩子的哭声还有人情味儿。我手抓着电车厢里的皮带环,眺望着在天尚未全黑时便点上了电灯的麴町的家家户户。于是这时候不由得更想起了“什么人都有”这句话。
三十来分钟后,我在表姐夫的家门口站着,按着水泥墙上的门铃。在门外隐隐约约听得见里边的铃声,从门玻璃上看到门口的灯亮了,接着一个老保姆把门开开一条缝看了看后,“哎呀……”一声嘴里冒出个感叹词,马上就把我让到了二楼朝街的房间。我把外套和帽子扔到桌子上的时候,一下子感到已经忘记了的疲倦,保姆给煤气取暖炉点上火之后出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多少有点儿收藏癖的表姐夫在这间屋子里也挂了两幅油画和水彩画。我漫不经心地比较着这几幅画,才第一回想起了变幻无常这句老话。
这时表姐和表姐夫的弟弟一前一后走了进来。表姐好像比我想象的从容得多,我尽可能准确地给他们转达了表姐夫说的话,并商量以后该怎么办,表姐并没有特别积极地表示出着急该怎么办的样子。反而在谈话的间歇拿起我的俄国羔皮帽,和我这么说着话:
“好奇怪的帽子,这在日本做不出来吧?”
“你说这个?这是俄国人戴的帽子。”
可是表姐夫的弟弟却是个比他哥哥还善于策划的精明人,他对事情的种种不利因素作了估计。
“最近哥哥的朋友让xx报社会部的记者把他的名片拿来了。那张名片上写着:堵嘴的钱里他自己已经出一半儿,请把剩下的交给他。”我查了一下,和报社记者说话的是我哥哥的朋友本人。当然他并没交那一半儿的钱,只是让记者来拿另一半的钱,那个记者也是的……”
“我可也算是个记者哪,那些难听得就请别说了。”
我为了抬高我自己,就不能不开点儿玩笑,但是,表姐夫的弟弟带着酒气的眼睛瞪得通红,说话就像演讲一样。这大概是因为平时连玩笑都不能随便开的爆发。
“再说还有为了要把预审法官惹生气,故意去找法官为我哥哥的辩护的家伙呢。”
“要是你能出面说说的话……”
“不,我当然说了。我一边低头行礼一边说,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好意,但是要是让法官不高兴的话,结果反而会辜负大家的一片好心的。”
表姐坐在煤气取暖炉前,拿我的俄国羔皮帽当玩具玩儿。坦白地说,我和表姐夫的弟弟说着话,心里边就担心这顶帽子。我时时在想着——要是掉到火里的话那就惨了。这顶帽子是我的朋友到柏林的犹太人街找过之后,偶然在莫斯科才好容易弄到手的。
“你这么说也没用吗?”
“岂止是没用,他们还说我们为了你哥哥费尽了力气,你这么说简直太失礼了。”
“原来是这样。那就什么也不能说了。”
“什么也不能说。因为这当然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也不会成为道德上的什么问题。在外人眼里看的话,他们为了朋友又花时间又费力,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为朋友挖陷阱帮忙。——我就算是个奋斗主义者了,可是碰到那帮家伙简直一动也不能动。”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外边“T君万岁”的喊声让我们吃了一惊。我一只手掀起窗帘,眼睛隔着玻璃往下边的街上看,只见一大群人把窄窄的街道挤得满满的。另外还有几个写有“xx街道青年团”字样的灯笼在晃动。我和表姐他们相互看看,忽然想起了表姐夫还有个xx街道青年团团长的头衔。
“不出去道个谢不太好吧?”
表姐终于露出“受不了了”的表情,眼睛来回看着我们两个人的脸。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表姐夫的弟弟大模大样地冲出了房门。我对他的那种奋斗主义感到有些羡慕,眼睛尽量不去看表姐而看着墙上的画。可是什么话也不说,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但是,要是为了说点儿什么,结果两个人都很感伤的话,那对我就更痛苦了。我默默地点上烟,注意到墙上的那幅——表姐夫的肖像画的远近法有些不对。
“我们哪儿是什么万岁的时候啊。这么喊真是没办法……”
表姐终于跟我说话了,只是她的声音很假。
“街上的人还不知道啊?”
“有可能……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
“T的事啊。孩子他爹的事。”
“这事要是从他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可能有不少内情呢。”
“真的吗?”
我不由得有点儿急了,转身背对着表姐,走到了窗前。窗子下的人群仍然在喊着万岁而且还是一次连喊声万岁。表姐夫的弟弟走到大门前,对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灯笼的一大群人行了个礼。表姐夫的两个小女儿被他左右牵着,时时把梳着小辫儿的头低下去……
后来不知又过了几年,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表姐夫的客厅里叼着近来才开始吸的薄荷烟,和表姐面对面地说这话。过了头七,家里静得让人觉着害怕。在表姐夫的白木牌位前的一盏油灯亮亮的。在摆着牌位的桌子前,两个女孩儿披着被子。我看着明显老了的的表姐的脸,忽然想起了那时苦了我一天的事。可是我嘴里说出来的却是不疼不痒的话:
“抽薄荷烟斗,凉气就像往身子里渗似的。”
“是吗?我的手脚也是冰凉的。”
表姐无精打采地整理着长火盆里的炭……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7年6月) 译者:宋再新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