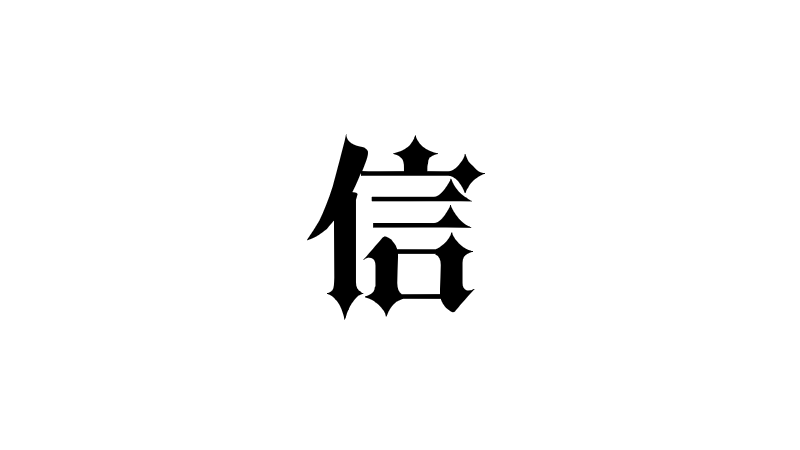
信
信
我现在住在温泉旅馆。我并不是来避暑的。不过,我倒是的确想在这儿安静地看看书写写东西。据这儿的旅行指南的广告说,这里对神经衰弱的人很好。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还住了两个疯子。其中一个是二十七八岁的女人,这个女人什么也不说,整天就是拉手风琴。不过,这女人的打扮还很得体,大概是哪个相当富裕人家的太太吧。我见过她两一次,总觉得她什么地方像个混血儿,脸长得轮廓分明。另外一个疯子是个头顶又红又秃的四十来岁的男人。这个男人的左手腕上刺有松树叶的刺青,从这点上看起来,他在没疯之前可能是干什么霸道买卖的。当然在澡堂里我和他经常碰到。有一回K君(他是住在这家旅馆的大学生。)手指着他的刺青突然问他:“你的太太是叫阿松吧?”一听这话,那个男人泡在水里,脸像小孩子一样红了……
K君是个比我小十岁的年轻人,他和同样住在这家旅馆的M子母女的关系相当好。M子用过去的话来说长个娃娃脸。我听说她上女学校时在梳辫子的头上缠上白布带练习木刀,当时心想,她那时肯定像牛若丸[1]或是其他什么人。另外S君和这个M子母女也有来往,S君是K君的朋友。只是和K君不同的是——我总是看小说,小说里为了要区别开两个男人的时候,就把一个说成是胖子,另一个写成瘦子,实在有点儿滑稽。然后如果一个人豪放的话,那么另一个人就会纤弱,这也让人忍俊不止。实际上K君和S君两个人都不胖,而且两个人生来神经都很易受伤害。不过,K君不像S君那样轻易把自已的弱点暴露出来。实际上他好像正在锻炼自己不暴露出弱点。
K君、S君、M子母女——我来往的就是他们这几个人。不过虽说是来往,其实唯一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一块儿散散步、聊聊天儿。因为这儿除了温泉旅馆(也只有这一家)外,连咖啡店都没有。我对这样清静倒没什么不满意的。可是K君和S君却常常感到所谓“我等对城市的怀念”之类。M子母女也——M子母女的情况有点儿复杂。M子母女是贵族主义者,所以她们在这里是不会感到满意的。可是在不满之中又感到了满足。至少算起来,她们前后满意了一个月。
我的房间在二楼的一角。我面对这间屋子角落的桌子,只有上午能够好好用功。下午,铁皮屋顶正当太阳暴晒,在那种热如火烤的时候根本没法看书。那么这个时候干什么呢?请K君和S君到我这儿来玩儿扑克或者日本将棋来打发时间,再就是枕着组合式的木枕头(是这儿的名产)睡午觉。五六大前的下午,我还是枕着木枕头,在看厚厚的皮纸封面的《大久保武藏镫》。这时,我房间的拉门一下子被推开了,伸进头的是住在楼下的M子。我这下子可狼狈了,傻乎乎地爬起来坐端正了。
“哎呀,他们不在这儿啊?”
M子把拉门开着,站在檐廊上。
“这间屋子这么热呀?”
背光站着的M子耳朵看上去红亮红亮的。我感到了一种近似义务的感觉,就站到了M子的身旁。
“你的房间凉快吧?”
“哎,……可是,整天是手风琴的声音。”
“啊,是那个疯子的对面哪。”
我们这么聊着,就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当西晒的铁皮屋顶波浪似的闪着光。这时,从长了叶子的樱树上掉下一只毛毛虫。毛毛虫在铁皮屋顶上轻微地发出声响,一下子就死了。死得实在是难看,同时死得也实在无奈——
“就像掉进了油锅一样。”
“我最讨厌虫子了。”
“我都敢用手捉。”
“S君也这么说来着。”
M子认真地看着我的脸。
“S君也敢哪。”
大概M子觉得我的回答没她希望的热情(其实我对M子——应该说对M子这样的少女的心理很感兴趣),于是几分赌气似的离开走廊栏杆:
“那就再见。”
M子走了以后,我还是枕着木枕头,接着看《大久保武藏镫》。但是,眼睛虽然看着铅字,心里老想着刚才那只毛虫……
我散步大体总在晚饭前。这个时候M子母女、K君和S君也都一块儿出来了。散步的地方只有这个村子前后两三百米的松林。这大概是看见毛虫之后或之前的事。我们仍是一边说笑着一边在松树林里走着。我们?——当然M子的母亲是例外。这位太太看起来至少比她自己的年龄要大十岁。我是对M子一家完全不了解的人。可是据不知什么时候看的报上报道,这位太太不是M子的哥哥的生母。M子的哥哥因为考大学没考上,用他父亲的手枪自杀了。要是我的记忆可信的话,报上报道说,哥哥自杀与这位来当继母的太太有责任。那么这位太太这么苍老或许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每当看到这个年纪还没过五十、但是头发已经白了的太太时,就常想起这件事。不过我们还是聊起来没个完。这时M子好像看见了什么,喊了一声:“哎呀,我怕”,一下子抓住了K君的手。
“什么呀?我还以为是蛇呢。”
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只是沙子上有几只小蚂蚁要拽一只半死不活的赤蜂。赤蜂仰面朝天,不时扇响要被撕裂的翅膀,要赶走蚂蚁群。但是,刚以为蚂蚁群被赶跑了,可转眼间蚂蚁又爬到了赤峰的翅膀和腿上。我们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赤峰挣扎的样子。这时M子也不像刚才了,她脸上认真的表情看上去很怪,还站在K君的身旁。
“老伸出刺来呢。”
“蜜蜂的刺是带钩的。”
我看大家都没说话,就对M子这么说了一句。
“算了,走吧。我最不喜欢看这种东西了。”
M子的母亲比谁都先走了。我们当然也跟着走了。松林里只留下一条路,其余的地方全长着挺长的草。我们的说话声在松林里回声格外响。特别是K君的笑声——K君在跟S君和M子讲着自己妹妹的事。他说在老家的妹妹好像刚从女学校毕业,对要成为自己的丈夫的要求是必须是不抽烟也不喝酒、品行方正的绅士。
“那我们都不及格喽?”
S君对着我说,可是我的眼睛里,他脸上却是一副很无辜、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烟不抽酒也不喝……那是拿来挖苦我这个当哥哥的。”
K君又突然加了这么一句,我只好随口应付着,渐渐地觉得这次散步成了苦差事。所以当M子说了一声“回去吧”的时候,我轻松地喘了一口气。M子还是满脸天真的表情没等我们说什么就一转身往回走了。可是在回温泉旅馆的路上,她只和她母亲一个人说话。我们回去当然还是走松林里的路,但是那只赤峰已经不知哪儿去了。
半个来月后,大概是因为天气阴沉沉的关系,干什么都没劲儿。我下楼,到有池塘的院子里。这时看见M子的母亲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看东京的报纸。M子应该是和K君和S君一起爬温泉旅馆后面的Y山去了。那位太太一看见我,就摘下老花眼镜和我打招呼。
“把这把椅子让给您吧?”
“不必客气。我坐这儿挺好。”
我坐在了正好在那儿的一把旧藤椅上。
“昨天晚上您没睡好吧?”
“不……出什么事了吗?”
“那位疯男士突然冲到走廊里了。”
“有这事?”
“就是,听说是因为看了报上登的哪家银行发生了挤兑开始的。”
我想象着那个刺了松树叶刺青的男人是怎样的一生。接着,——让你见笑了,我又想起了我弟弟手里的股票。
“S先生也发了牢骚呢。”
M子的母亲总是婉转地向我打听S君的事情。我不管什么样的回答都要加上“可能吧”、“我想……”之类的话。(我总是觉得看一个人只能看这个人本人,自然就对什么家族、财产、社会地位之类的不感兴趣。我觉得特别恶劣的就是即使是看这个人本人,也总是在这个人身上找和自己相似之处,随意地决定好恶。)另外我还觉得这位夫人的想法——想打听S君身世的想法很可笑。
“S先生好像有点儿神经质吧?”
“噢,怎么说呢,有点儿神经质吧?”
“他真是一点儿都没沾染上社会的坏习惯呢。”
“要不怎么说是大户人家的少爷呢。……不过我觉得他社会上基本的东西已经懂了。”
在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水池边有一只小螃蟹在爬,而且这只螃蟹正把另一只螃蟹——一只壳已经快碎了的螃蟹一点儿一点儿地拽走。我忽然想起什么时候看过的克鲁泡特金的《相互扶助论》里讲的螃蟹的故事。据克鲁泡特金讲,螃蟹总是去帮助受伤的螃蟹伙伴。可是又有一个动物学家根据自己观察的实例说,螃蟹是为了吃受伤的伙伴才去拽它们的。我看着两只螃蟹渐渐爬进菖蒲的荫凉不见了,一边还在和M子的母亲聊着天。可是不知不觉我已经对我们的谈话兴趣索然了。
“他们要天黑才回来吧?”
我这么说着站了起来,同时我感到了M子的母亲脸上的一种表情。那是一种有点儿惊讶同时又闪现出一种本能的憎恨的表 情。但是这位夫人立刻就沉稳地回答:
“是,M子也是这么说的。”
我一回到房间,手抓着檐廊的栏杆,眺望着在松林中隆起的Y山山顶。快要落山的太阳光斜照在山顶的岩石堆上。我看着这景色,心里忽然涌出对我等人类的怜悯之意来……
M子母子和S君两三天前一起回东京去了。K君要在温泉旅馆等她妹妹来会合(大概要比我晚回去一个星期左右),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去。只剩下我和K君两个人的时候,我才感到几分放松,当然我想安慰K君,但反过来又怕无法回答K君。不过和K君在一起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特别是咋天晚上和K君一起一边洗澡,一边还讨论了一个小时的弗兰克[2]。
我现在我的房间里给你写信。这里已经入秋了。今天早晨醒来时,发现我房间的纸拉门上倒映着小小的Y山和松林。我趴着点上一支烟,看着这清爽的、小小的初秋景致,感到了不常有的宁静……
那就写到这儿,再见。东京的早晚大概已经好过多了吧?请代向孩子们问好。
作者:芥川龙之介(1927年6月) 译者:宋再新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